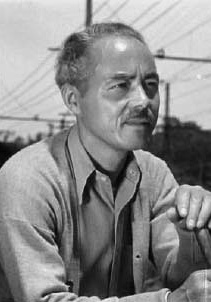祇园歌女 祇園囃子(1953)
简介:
- 母亲离世,父亲生意失败、疾病缠身,十六岁的荣子(若尾文子 饰)走投无路,只好到祗园投靠母亲生前的艺妓姐妹美代春(木暮实千代 饰)去做见习艺妓。经过美代春的悉心培训,一年后,荣子成为了一名亭亭玉立的艺妓。终于到了荣子第一次接待客人的这一天,美代春领着荣子接待了两名客人——楠田和佐伯。后来美代春和荣子跟着楠田到东京游玩,到达当晚在旅店内,楠田想与荣子发生关系,荣子不肯就范,在反抗中咬伤了他。因为这件事,美代春和荣子的生意大受影响,她们只得闲赋在家。饱受门庭冷落的荣子决定上门亲自道歉,而美代春得知后,急忙赶去替换了荣子。次日,荣子询问一夜未归的美代春是否为了自己而出卖身体。美代春的一番话,让荣子学到了作为艺妓的一套人生哲学。
演员:
影评:
- 小津曾说:“我拍不出来的电影只有两部,那是沟口的《祗园姊妹》,和成濑的《浮云》。”
拍摄于1953年的《祗园歌女》是导演沟口健二后期的作品,貌似是一部比较“低调”的电影。同小津安二郎相比沟口要幸运的是,《西鹤一代女》、《雨月物语》以及《山椒大夫》在国际重大电影节上大放异彩,让其扬名世界。
《西鹤一代女》以史诗的形式波澜壮阔地描绘出一个女人的一生和日本的历史,《雨月物语》展现出女性在战争中的悲惨命运,《山椒大夫》刻画了封建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相比这些,《祗园歌女》的格局要小得多,它仅仅描绘了东京都吉原街区的两个普通艺妓的生活点滴。
但是当我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还是被深深打动了,可能也跟个人的喜好有关,格局小的电影往往细节饱满,人物刻画细腻,有种“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的感觉。可能这也是东方人的审美习惯,比较在乎意境和情绪而不是宏大的史诗。
背景
导演背景:
导演拍电影的目的有很多种,有位影评人说侯孝贤拍《童年往事》,是在拍他生命过程中的一个韵律,就像脉搏的跳动。我想世界上所有的好导演其实都是在做这样一件事吧,只是把自己的脉搏与电影一同跳动,自己的血液渗入到电影的每一帧画面中。
大岛渚曾经对照小津和沟口两位大师作如下评论:“小津只在自己喜欢干的事情范围内工作,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所以是幸福的;但是沟口一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盲乱地努力着,所以说他的一生过得很辛苦。”
与家境良好的小津成为鲜明对比,沟口的成长经历非常坎坷。他的家境非常穷困,17岁时母亲因为过度劳累而去世,父亲丧失劳动力,沟口唯一的姐姐承担起家庭的重任,成为了一名艺妓,之后又成为了贵族的小妾。
沟口与父亲关系非常恶劣,同姐姐的关系却很好,他寄宿在姐姐家很长一段时间。正是这样的经历反映到沟口的作品里,男性总是卑鄙拙劣的,而女性却善良,坚强,宽容,成为男性的拯救者。
关于沟口还有一个轰动一时的事件就是曾经与沟口交往密切的京都妓女百合子用刀刺伤了沟口,沟口后来说到此事:“那天,从背上流下来的血腥红猩红地染了一地,我一生都无法忘记那种红色,苦难的、悲伤的,但是微弱的透着温暖。”就是这微弱的透着温暖的血液教会了沟口如何理解女人以及如果通过电影展现女人。
故事背景:
《祗园歌女》为我们展现了日本艺妓的世界。
故事以16岁的荣子来到母亲生前的好友美代春住处求其收养自己并跟随美代春成为一名艺妓为开头。
艺妓往往深居简出,不工作的时候便在家里,于是荣子来回穿梭在京都的各个巷子里寻找美代子的住处,然后有一个荣子的主观镜头,是茶社写在木匾上的艺妓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到美代子的名字上有一个圈起来的“甲”字,这说明艺妓是分等级的,而美代子无疑是她所在的茶社中比较高等级的一个。随着荣子找到美代子的住处,我们也随之进入艺妓那神秘,不为人知的世界。
之后荣子开始了漫长艰苦的艺妓学习过程。古时艺妓学习由十岁开始,到后来改为十四到十五岁,荣子十六岁,刚好开始学习。艺妓要学习掌握的内容繁多。其中包括文化、礼仪、语言、装饰、诗书、琴瑟,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严格要求。初为艺妓者称为“舞妓”,而后才可以正式转为“艺妓”。艺妓生涯一般到30岁完结,在30岁以后仍然继续当艺妓的话便降级,成为年轻貌美的名妓之陪衬。艺妓中把前辈艺妓称为“姐姐”。片中的美代子即荣子的“姐姐”。她们相依为命、互相扶持。
我们看到荣子在茶社老艺妓的教导之下学习茶道,击鼓,弹琴等等。老艺妓同学习的少女们这样说道:“你们就代表着日本的美,这是活生生的艺术,是文化宝藏。”荣子正是抱着这样美好的幻想勤奋地学习,而她之后不得不从这样的幻想中抽离出来的时候让我们唏嘘不已。
艺妓在过去的确是卖艺不卖身的,当然这不是说艺妓就没有性生活了,一般而言,与艺妓有性关系的都是签订过契约的固定的一个人,他被称为保护人,会为艺妓的生活起居负担相应的费用,艺妓的生活能力一般比较差,会有好几个佣人伺候着,因此和艺妓有密切关系的往往都是显赫的名流。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茶社的业主逐渐利欲熏心,很多艺妓开始走上娼妓的道路。等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市场经济在日本的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由金钱所取代,艺妓更多的成为了娼妓。不论她是自愿的还是被逼的。影片中祗园业主老板就成为了使艺妓走上娼妓道路的帮凶,在片中她曾跟美代子说,这年头,哪个艺妓不干那一行(指卖淫),实属悲哀。
本片中的男人
日本电影中的男人的形象似乎是矛盾的,既有黑泽明《七武士》中那样阳刚的男性形象,也会有沟口健二电影中懦弱,卑鄙,拙劣的男性形象。
片中荣子的父亲算得上一个典型,在荣子的母亲出嫁给她的时候美代子她们还都很羡慕,认为荣子的母亲会有一个幸福的归宿。结果却是一场幻影,荣子的父亲在片中居然这样说道:我很久都没有和那里有关联了,她不过是一个艺妓而已。可见荣子的父亲并没有给荣子的母亲带来幸福。换言之,艺妓要获得正常的家庭幸福是几乎不可能的。荣子的母亲早逝,荣子的父亲既让女儿承担自己的责任还漠视女儿因此受到的伤害和误解。在影片的开头,荣子为了改善自己的情况而来求助于美代子,荣子父亲却不同意,但是到了后来自己女儿当上了艺妓他生意失败时却反而厚颜无耻地来向美代子讹钱,善良的美代子此时已经捉襟见肘却将自己的首饰给了他。可见他之初不同意荣子当艺妓根本不是出于父亲对女儿的关心,而是出于对自己面子的维护,到了后来觉得自己女儿有利可图的时候露出了虚伪卑鄙的嘴脸。
荣子开头去找美代春时,与美代春争执的男人可以说就是年轻时候娶走荣子母亲的荣子父亲。他们道貌岸然地说会娶她,口口声声地说是真心爱她,企图让无知的艺妓被这样的谎言所蒙蔽。而然他们是不可能信守他们的誓言的,爱情的承诺只不过是美丽的肥皂泡。在影片后来,美代子陷入困境的时候,当初说要娶她的这个男人却拿着冰淇凌来羞辱她,可见这男人的行径有多么龌龊。
片中另外的男人形象跟前者又不一样了,他们是处在市场经济中的代表着新时代的商人,他们揭示了艺妓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有别于过去的压迫和处境。
他们西装笔挺,谈吐得体,骨子里确充满了对金钱和肉欲的贪念。他们更加的道貌岸然,充满着更加令人发指的巧妙的欺骗。
他们其实同荣子的父亲还是同一个人,只是换了一身好皮囊而已。
祗园的女老板在片中与商人勾结在一起,即使她曾经也是艺妓,而现在却成了欺压艺妓的商人的爪牙和帮凶。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或许就跟曾经受婆婆欺负的媳妇终会成为欺负媳妇的婆婆一样充满着反讽和悲哀。女人的命运真的要这么轮回下去么?
本片中的女人
本片完美地刻画了两个姐妹情深的艺妓——美代春和荣子,在本片中,美代春和荣子有着各自不同而且多重的身份,深入的反思了日本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
美代春是本片中的主心骨,她美丽,善良,聪明,坚强。她是艺妓,迫于无奈也成为了妓女,她还有另外的身份——姐姐。她承担起了本应该是男人承担的责任,勇敢地承担了照顾荣子的责任。她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荣子,为了荣子甘愿牺牲自己。她看透了世事却无力改变这样的世事而不得不妥协。她成为了男性的拯救者,在荣子父亲无耻的向她讹钱的时候她慷慨地帮助了他。影片之初似乎将她刻画成一个冷漠的爱说谎的艺妓,但是实际上她是最有人情味的一个,他的佣人道出了真理,她在那个男人三个月还没有付钱的情况下还对他彬彬有礼。她之所以不信任那个男人是因为她早已经看透了一切,不对男人再有天真的幻想。
美代春成为了荣子的保护者,成为了不幸的承受者,她或许就是沟口姐姐在电影中的投射。
荣子本是天真可爱的少女,她本来的身份应该是女儿。可是她的父亲却是她的世界中无能的权力拥有者。她年轻血液里流淌着反叛的因子。她对生活充满向往和热爱,她认为艺妓是美的象征,在祗园刻苦地学习一切技能为的是成为出色的艺妓。当真正残酷的现实世界向她展开时她企图反叛,她咬下了可耻之人的舌头。却无法做到真正的“革命”。最后她只能屈服于这样的现实。充满着悲哀。
沟口在本片中没有给出一个希望的结尾,美代春以屈辱的代价换来了重新开始的生活,最后美代春与荣子姐妹两个并肩盛装的消失在吉原街区的夜色里。或许这又是一个不可逆转地轮回。
美代春和荣子无法反叛这样一个世界或者可以说是导演沟口无法反叛这样一个世界,甚至在某一点上,沟口虽然对女性充满了同情却也深深陶醉在她们无畏的勇敢之中。这是日本社会所无法规避的民族心理。
本片在电影史中的意义
首先,本片与其他日本女性电影一道构成了日本女性电影的谱系。
在日本的文化中,对女性是有种奇怪的心理的,即敬而虐之的心理(不妨想想日本的AV片,以及诸位对AV女优的心态)。他们喜欢把女性塑造为女英雄,充满磨难与压抑,可是他们明知女性的处境却永远不会去改变她们的处境,甚至陶醉在那种苦难之中,就好像日本的军国主义宣传片中展现战争都是展示战争残酷可怖的一面。英美人感到迷惑不解,这军国主义的电影怎么拍得像反战片似的,他们其实是不懂日本人的心理,我曾经看过一本小册子采访靖国神社供奉的战犯的母亲,她们一个个都很陶醉于自己的儿子战死在战争中,能供奉于神社对于她们而言是莫大的容光,也就是说,日本人觉得效忠于天皇是他们一辈子最大的荣耀。说白了,就是一种自虐心理。在中国,忠和孝的前提是“仁”。而日本人不一样,他们的忠和孝更为极端,也就导致了这样一种心态。
小笠原隆夫的《日本战后电影史》一书中提到了日本电影中的被虐者谱系,罗列了这样几类女性:军国主义下的女性,如《大曾根家的早晨》,封建习俗下的女性,如《晚菊》,贫乏的日本社会下的女性,如《女人的园》,时代的发展历程中的女性,如《二十四之瞳》,在这其中时代发展历程中女性的刻画最多也最为出色,如成濑巳喜男的佳作《乱云》也属其中,而这部《祗园歌女》更加如此。
纵向地放入这样的谱系之中,我们能清晰地找到女性在不同时代下所承受的一切,能历史地角度较全面的把握和论述日本电影的某一个方面。
另外在电影语言的角度,这是沟口较成熟的一部片子,其个人风格已经形成。主要有长镜头,全景主义,多点拍摄,定机位拍摄,低机位拍摄。
此片的长镜头比比皆是,室内室外都有,例如美代子带着初次盛装打扮的荣子在街道拜访的时候镜头就跟着主人公游走,主人公到哪,镜头就一直跟到哪。基本做到了一个场景一个镜头。沟口早期的电影中还是比较推崇蒙太奇的,越到后来才慢慢开始喜欢用长镜头,他觉得长镜头可以不打破演员的表演。法国的影评人曾经非常推崇沟口的长镜头,可沟口的长镜头可不是来源于巴赞,他的长镜头来源于日本传统的戏剧。
本片22分钟是一个艺妓表演的场景,摄影机设在所有人的背后,处在正中间的是男客人,而整个镜头就像一个舞台,看电影的人好像是坐在第二排的观众。艺妓表演的整个场景被记录下来,这就是沟口的全景主义,他习惯把人物的动作完整记录下来并且展现人物与当时环境的关系。
多点拍摄在多人对话场景中经常遇到,在荣子初次拜访美代春的时候,拍摄荣子与美代春的对话沟口采用的机位完全不同于美国好莱坞的常规法则,美代春、荣子、佣人分别坐在茶几的左中右三个方向,第一个镜头在三人正面中间偏左的位置,将三个人的位置关系交代清楚,第二个镜头直接处在佣人的位置,确明显不是佣人的视角,将佣人完全去除在场景内,到了第三个镜头却到了三人的背面偏右的位置,三个镜头几乎是围绕人物一周。这种拍法在小津的片子里也出现过,《东京物语》中老头老太太和儿媳的对话一场戏也是类似的拍法。这样的拍法最大限度地展现了演员的表演,突出人物关系,人和环境的联系,而不是将观众带入故事情境中。
定机位可以说是形成沟口电影风格重要的一点,就像日本的诽句和水墨画(其实老祖宗就是我国的诗和国画)一样,镜头内部有着某种形式化的美感,这种东西是美国人和欧洲人弄不来的。回到刚刚说过的第22分钟的艺妓表演的那个镜头,在那个镜头里屏风处在正中间位置,两个艺妓在屏风前面翩然起舞,整个构图非常对称,典雅,简洁。充分体现了东方人的审美趣味。在第29分钟,美代子和祗园的业主一块去寺庙,镜头里长廊、柱子等形成的线条也构成了独具风味的东方美。
低机位拍摄在这部片子中比较明显,甚至跟小津的机位有些相似,但小津的低机位展现的是日本寻常人家的生活点滴,给人亲近平和之感。本片的主人公局促在狭小的房间内,低机位反而突出了艺妓生活场所封闭,压抑的感觉。
沟口的电影风格跟其他的电影大师,如黑泽明,小津等等一道构成了日本电影的风格,有别于欧洲电影,美国电影,日本电影与其他亚洲国家电影一道展现了东方人看世界的方法和视点。
美国人总是希望将自己的普世价值影响到全世界,好莱坞的做法就是冲进每个国家的电影院,这对全球文化的多样化和电影的发展是不利的。很多区域在美国电影的冲击之下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比如台湾电影。试想如果世界上每个地方的电影人生产出同样风格的电影会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想把沟口的电影放到日本电影,放到东方电影的谱系之中并与其他区域特别是主流文化区域做比较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一直以来,欧洲和美国的电影理论比较系统和深厚,而东方电影或者其他比较弱势的区域似乎从来没有形成自己成系统的理论,这可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通常聊到艺伎,女人是面露不屑又带着艳羡,男人则显出猥琐的神情,仿佛暗示见不得光的勾当。事实上,艺伎从事表演艺术,学的东西很多:插花、茶道、舞蹈、音乐、礼仪……学成出来,艺妓比一般的贵族小姐要淑女、懂礼和渊博。正如片中所说,“你们(艺妓)代表着日本的美,这是活生生的艺术,是文化宝藏”。
《祇园歌女》有段我百看不厌的场景,说荣子初入艺伎行当,在美代春、保姆和乐师的指导下学习各种门道,甚有美感。这段戏,沟口健二用的不是那种快速剪辑加激昂音乐,他的节奏轻拢慢捻,不慌不忙,拍出了日本茶道、花道那种形式的美感。沟口出身底层,拍的也是底层,但比起中产的小津安二郎,他的镜头保留了日本传统社会残留的美。艺伎就是传统美的象征。小津的意识更贴近当代,所以他在西方也更受欢迎,被视为东方的代表。
《祇园歌女》的时候,是艺伎这行当污名化的时代。当艺伎费钱,荣子入行,置装费就要30万日元,多亏了美代春央求茶行老板,茶行老板托了富商,才筹得入行之资,否则即便生得貌若天仙,也不得门而入。但也正是因为艺伎从业耗费不菲,依靠茶屋表演得到的收入,是支撑不了生活的。荣子还未晋身艺伎,就听得同行说茶屋老板帮她找了“旦那”,即包养的老板。旦那是多数艺伎的生活来源,代价是向他出卖身体。有的艺伎退休后,还会嫁给旦那,荣子的母亲可能就是如此。荣子同行惴惴不安的原因,是因为她的旦那是个60多岁的老头。
美代春是当红的甲等艺伎,所以俭省一点,是不必找旦那的,还能将落魄的主顾扫地出门。如果剧情就此发展,电影是没有冲突、没有戏的。鲁迅说中国男人有两大爱好:拉良家妇女下水,劝风尘女子从良,这两大爱好其实暗合了人们“看戏”的心理。戏就是要有变化,要有不合规矩但合情合理的变化。拉良下水、劝妓从良,女人的转变恰恰佐证男人的性魅力。背地里,“艺妓有谁不被碰的?”,偏偏美代春坚持底线,她“之前不是没有做过”,但依然衷心不改。美代春的坚持构筑了影片的基本冲突,而这份难能可贵的坚持最终被打破时,悲剧就显露出来,高贵就显露出来。
沟口若是直写美代春的被迫下沉,则显得不够精巧了。他卖个关子,先拍荣子。荣子负责引领观众逐渐进入艺伎的生活,本身由天真烂漫的少女,逐渐认识到了成人世界的残酷。许多作家、导演喜爱这类故事,拍年轻人心底梦想破碎的声音,这也是很好的,但沟口只是把它当个引子。荣子咬伤了茶行的大主顾,大主顾躺在床上顾不得指责荣子,反而把斗争焦点指向了美代春。原来美代春推开了主顾的要客,令他的生意损伤惨重。这场戏中,藏了半部电影的冲突终于图穷匕见,亮出全片最尖锐的矛盾,沟口的叙事技巧真是令人叹服。
好电影的本质冲突大同小异。人物向上,时代下沉,人物百般挣扎,最后迫于压力,和光同尘。公认史上最伟大的电影《教父》,说一个努力想摆脱黑帮的儿子最后被迫接下家族衣钵、满手鲜血。《教父》的魅力经久不衰,近半个世纪后依然被奉为“男人的圣经”,是因为它说出了我们共同的真相:每个人都处于泥沙俱下的时代,试图逆流而上,最后遍体鳞伤。《祇园歌女》是个短小精悍的小品,故事不拖泥带水,场景仅限室内,也拍出人之于时代的渺小和无力,可和《教父》般的史诗感不相上下。沟口以小见大的雄健笔力,可见一斑。
所以电影之道既在宇宙洪荒,也在一粥一饭。电影之道,近乎于禅。
《祇园歌女》的结尾,美代春侍寝归来,荣子追问她,二人一起抱头痛哭,既哭拗不过时代,也哭身为女性的命运。故事结束,就这样了。
说到艺伎,就想到清末上海的“长三书寓”(书寓与长三堂子,二者细较是有别的),那些被称作“先生”的高级妓女。再往前推,则有唐宋时期的官妓、营妓,《琵琶行》里“五陵年少争缠头, 一曲红绡不知数”,消费的似乎也只是才艺,——“教坊”这个名字取出来,本来只是文艺活动的地方呀。但是在一个传统的男权为主导的社会,事情的边界,就是这么容易模糊。
看沟口健二的《祇园歌女》,就特别容易联想到侯孝贤的《海上花》,两部电影同样将镜头瞄准了出卖色、艺的女子的日常生活,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个“性消费”的问题。
但是二者很不同的是,《海上花》小说原著主要是在写男女之情,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里,官人(嫖客)和倌人(妓女)并不只是金钱和肉欲之间那么简单的交换。张爱玲看重韩邦庆的小说,觉得他写出了一种“现代式爱情”的感觉。那种“男女情感的幽微之处”是其他小说不可及的。张爱玲在1979年写给夏志清的信里还说:“我一直觉得《海上花》除了写得好,还有气质好,但是没有pinpoint,它好在男女平等与不残酷上。”
侯孝贤把小说改编成电影,他也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侯说:“(上海英租界区)里的妓院,成了一个以女人为主体的生态环境。男人来这里不完全为了‘性’,更为了追求与‘性’同样迫切的另一种需要——爱情。社交生活占妓院最大的比例,女人与男人自由交往,自由恋爱。赚取男人的钱,擭得某种程度的经济独立,可以选择男人而嫁。这些,在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是不可能的事情,却在妓院这个边缘的角落发生着。何况还牵连爱情,所以到底足谁掌握了谁,谁支配了谁,就变得更复杂暧昧。此中,人与人的关系,自然是我最感兴趣的了。”
而《祇园歌女》不同,它的底色是批判,是男女之间的残酷和女性的没有出路。
艺伎这个行业的出现本身就是商品性的。17世纪,在东京、大阪这样的地方,出现了以“侍酒筵业歌舞”为职业的艺伎。而酒筵就是享乐与社交,高级的酒筵则是高级的享乐与社交,是社会资本的舞台,富商巨贾、上层政客,从资源的独占、高昂的支出、殷勤的服伺那里获得归属感和身份标签。《祇园歌女》里就生动地展现了这一点:富商们为了交接政客,送冰箱、送钢琴,还要请艺伎陪着寻欢作乐,还有性贿赂,艺伎的作用一目了然。
何况,日本这个民族,对“性”的感受是非常特别的,如果“性”分为生理和心理两部分,他们好像特别在意心理的这部分。这在很多方面可以看出,艺伎的和服,重重叠叠,像粽子一样裹得严严实实,却在后颈部却露出很大的一块,故意惹人联想。日本语中有“褄を取る’”(提起下摆)的话,引申之意就是成为一名艺妓。和服的下摆随风吹开的少许凌乱,再从这个凌乱的下方窥视到白皙的小腿,若风稍大点的话,还能窥视到更隐秘的部位——这才是日本人以为的最撩人的凄艳,也是他们最为迷恋的。
浮世绘中,从浴池里起身的慵懒娇憨的女体,作为一个整体酝酿出凌乱的构图也极为常见,这与和服下摆的凌乱是共通的,也就是日语中的“色気/艶めかしさ”。
所以,不要以为艺伎那种陪酒、音乐、歌舞、陪着做游戏等项,没有肉体的出卖,就不是对女性的消费,很多也是出于对性心理的满足。
而《海上花》里,不仅是长三,包括幺二(次一等的妓女),她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并不是完全靠出卖肉体。当时的交际场上,喝茶、吃饭、搓麻将、和人谈生意,往往会叫一两个妓女出场,装点门面,或者让她们演唱评弹或者昆曲之类,活络场面,这个就是叫局。所以我们看电影《海上花》里,帮佣们喊:“小先生出局”,或者“三先生出局”,声音是响亮高昂的,有一种职业的正当与自信。喊得越多,越证明自己生意好,是红倌人。
电影《祇园歌女》一开头,男、女之间的矛盾就摆出来,妹妹荣子因为叔叔的势利、父亲的无情,不得不投靠母亲之前当艺伎时期的姐妹美代春,这种选择的出发点是人生的自立,涉世未深的姑娘只把它当作是一种职业的选择。而两人的对话,则从侧面交代了母亲婚姻的不幸:结婚时千好万好,惹人羡慕,去世的时候,父亲居然连葬礼都不来参加,连夫妻关系都不想承认,还要卖掉唯一的女儿。这样的对照,无非是说明:对于艺伎的人生而言,婚姻也是一条难行的路。所以,当前面有一位主顾说要和美代春结婚时,美代春就是笑笑,他知道这件事情是雨天路面的水痕,雨下得再大,天晴就要干的。
电影对美代春的这位顾客的描画也是寥寥数笔,非常传神。他因欠了“茶房老板三个月的钱”,被美代春劝退,前面刚说要和美代春结婚,当美代春拒绝他之后,立马恼羞成怒,拿着衣服来用力地摔打美代春,“结婚”这样的话,也是随口说说的吧,爱与婚姻都是很重的承诺,他贪恋的无非是这种纸醉金迷温柔乡的生活。果不其然,这个人境况稍有好转,便拿一个冰淇淋来羞辱失势的美代春,男人都是什么样的动物啊?
当美代春答应荣子的要求,要竭力培养她之后,有一组表现艺伎学艺和生活的场景,拍得极美,用电影里的话说:“这是活生生的艺术”,我怀疑是拍摄的是真实的艺伎生活。沟口健二在这里拍出了一种日本的美,他更拍出了日本这种美的脆弱和虚幻,这么的易于崩塌。
东京之行,姐妹俩因不肯接受性需求而与大客户闹僵,大客户施压给茶房老板,茶房老板申斥美代春,说了三句话:
你是刚出道吗?
艺伎有谁不被人碰的?
你不是也被人碰过吗?
三句话问得美代春低头无言。
再红的艺伎(美代春是甲等,荣子正当青春貌美),再娴熟的职业技巧,再成熟的心智,又能如何?她们有选择客户的权利,但是也仅限于普通的客户,当男性强权突破自己无力反抗的边界的时候,她唯一能做的也只有屈服。
这部电影最值得赞赏的地方,在于美代春勇敢地充当了一个拯救者的角色。影片结尾美代春对荣子的保护,我觉得特别能理解,她在荣子身上有一种“共情”,是一种源于女性这种身份的保护。
电影中的几个男性形象是比较负面的,懦弱、市侩、狡诈、充满贪欲,而那个茶房老板,形象也是非常男性化,她用来摆布、教训不听话的艺伎,手法和男人又有什么两样?电影中与茶房老板相关的几个个细节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她看报纸,她像男人一样抽烟(当然不是说不可以抽烟、看报纸,证明她已经习惯、溶于男人的这一套),最后搞定了美代春之后,面有得色,手里在玩弄着折扇,那种玩弄于鼓掌之间的感觉,电影的塑造真是太精妙了。
与同时代的其他电影大师很不同的是,沟口健二看向传统的目光是彻底的、尖刻的,血淋淋的;在建构起来的繁复迷人的日本的美之上,他看到了无数的残骸,看到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残酷征服与镇压。
电影中很有趣的是,但凡是街景,就会有女人行走或者工作的场景,比如1′40″那个头顶着重物卖蟋蟀、鳗鱼的妇女,7′04″那个举伞行走的妇女,16′37″那个扫地的女子,18′37″与美代春姐妹打招呼的妇女,另一边有另外一个女子在驻足观看……这些似乎在表明,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了。
离电影拍摄的时代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到今天,希望人是有自由的,女人是有自由的。
自由地选择职业,自由地选择爱或者不爱,自由地选择性的对象。
- 我是第一次看沟口健二的电影。像小津安二郎,但小津比他更家庭,更中产;沟口健二拍的是底层,是歌女、艺妓、劳动妇女,是因为战争、乱世或者贫困的悲惨命运。他的镜头和构图,每一个都有讲究,比如荣子出道时被姐姐带着在街上挨家挨户打招呼时那个动荡的长镜头;比如荣子第一次见客人喝醉时倒在地板上,而姐姐在远处说话的那个极低的角度的镜头;比如客人和艺妓一起观看歌舞表演时那个在所有人后面的机位;还有落魄的姐姐没有生意时,在房子里独自弹三味线琴,长长的门帘垂下来的那个静止镜头。人类的审美天赋真是与生俱来的,和教育、职业、社会地位都没有什么关系;要不然,很难想象出身于东京贫民区,小学毕业就工作的沟口健二能有把电影拍得如此漂亮的能力。
沟口镜头下的女性是苦难的,也是作为审美的苦难。近镜头中是脸部的特写,看着他们,就能看见沟口生活在女性中、被女性救赎、与女性纠缠一生的命运。他自己的姐姐曾经是艺妓,以一己之身养活了一家人;他的镜头离她们那么近,仿佛是在拍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隔阂。所有的男性都作为反面角色出现,从混球的父亲到贪婪的资本家,女性被放在一个极高的地位上供奉着,即使陨落了,也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式的陨落,她们的美好作为精神层面上的信仰并未失去。
看沟口健二的电影,可以度过一个内心宁静的晚上。与炮火连天或者各种狗血的电视剧和电影不同,他的电影和小津一样,是安静的。没有特别剧烈的戏剧冲突,全剧线索简单,只有一条主线,情节就沿着这条主线慢慢展开;但观众不会觉得无聊,因为心情已被角色的命运牵动。导演的内心摆在那里,观众仿佛可以看见导演的嬉笑怒骂,为她们的命运而哭泣,为她们的振作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