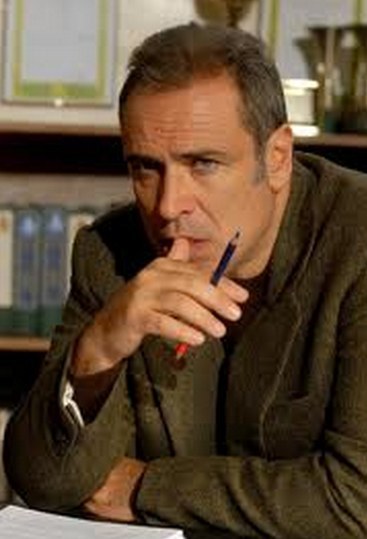肮脏的爱情 L'amore molesto(1995)
简介:
- 迪莉亚的母亲意外溺水身亡。那晚,她曾接到母亲的电话,得知母亲当时和一个男子在一起,却不知道那个男子是谁,她决心找出真相。
演员:
影评:
“我觉得这是现代女性身体的一个重要影像,象征着一个寻找自我的女性。黛莉亚先是通过男性化服饰掩饰自己,后来她在那个地下室的最深处,找到了母亲原本的身体。最后她意识到,她要接受自己和阿玛利亚之间的联系,母女之间的传承得到重建,那些难以言说的东西也得到了揭示。” 这是费兰特写给《讨厌的爱》导演马里奥的信中,所呈现的一段文字。
玛吉·吉伦哈尔导演处女作《暗处的女儿》出师则利,其原著便是埃莱娜·费兰特的小说。这位颇受影视圈改编青睐的作家却将自己掩进了神秘的面纱之下,至今未公开自己的身份和性别,这一事实意外地与《讨厌的爱》中所展现的朦胧感形成了互文。
《讨厌的爱》是费兰特的首部长篇小说,一经问世便迎来如炬的关注,立刻于三年后以电影的形式与观众见面。费兰特对人物内心在复杂人际环境中的焦灼与变化有着深刻的勾勒,正是这样细腻的,难以言说的东西在每一个那不勒斯人之间搭起了桥梁。
费兰特在信中提到的那些难以言说的东西被倾注在他的文本中,是成为黛莉亚与阿玛利亚之间的牵引,又或是成为自己与那不勒斯之间的羁绊,如蛛丝般强韧的真实情感变得不可言说,那是因为我们的视线不由衷地变得模糊。像是忘了佩戴眼镜的高度近视患者,蜷缩在自己的能见范围之内。
地下蛋糕店的大门被缓缓关上,年幼的黛莉亚撞见母亲与卡塞塔亲热,此时的她没有戴眼镜,眼前的一切被打了马赛克,剩下的唯有主观的代入。从地下室切换到黛莉亚在家中的场景绝非偶然,一切在黛莉亚即将结束那不勒斯之旅,最终留步于地下室之时昭然若揭。黛莉亚被蛋糕店主性侵,而她不自觉地将母亲与卡塞塔的亲热场景代入,来掩盖自己的伤痛,记忆像视力一样出现了偏差。
我并不愿意将黛莉亚的近视眼设定当作时一种偶然,更愿意相信是她自身的指喻,或者说是她根植情感的藉口。如信中所说,黛莉亚一开始总是用男性化的服饰掩饰自己,在她的童年记忆中,父亲一直是一个艺术家的形象,从某种程度上成就了她以后的漫画家身份,在这个立场上,黛莉亚对自己的父亲是崇拜的。尤其在当时的那不勒斯,男性主义的味道相对浓了一些,引用费兰特的肺腑:“您通过一种高超的艺术手法,展现了一位女性在不同男性之间进行调查的过程,这些男性代表那不勒斯过去最糟糕的一面,一些不可救药的人。您展示了卡塞塔、舅舅、安东尼奥,还有父亲的身体,换一句话说,您展示了在一种爱恨交织、逞强凌弱的关系里,他们呈现的样子。” 女性被千人千面的男性所裹挟,黛莉亚只能选择性的仰望着父亲,而母亲,也就成为了父亲和大家口中的母亲。马里奥通过几场梦境和几场回忆来表现这种情感的覆盖。梦境中,卡塞塔尾随着母亲和自己,母亲欲迎还拒的笑声……回忆里,母亲在公交车上对陌生男人的笑容……黛莉亚能够认为父亲画笔下风姿绰约,袒胸露乳的吉普赛女郎就是母亲,也不见得奇怪了。
黛莉亚换上红裙在雨中奔跑,在男人之间的冲撞下摔碎了自己的眼镜,由此,她踏上了认知重塑,审视过去的路程。她对着镜中的自己微笑,显得十分满意,此刻,视线仿佛不再模糊,红色的自己非常耀眼。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认为眼镜只是根植情感的藉口而非客观设定。小安东尼奥眼看就要被舅舅扔下楼梯,楼下的母亲声泪俱下,依然不妨碍黛莉亚抬头望着楼上所发生的一切,继续仰望着她的父亲。童年的黛莉亚即便带上眼镜依然只能看到自己心中认定的事实,而现在的黛莉亚失去了眼镜的辅助,却更能看清自我,在那不勒斯喧闹的大街上自由穿梭,去正视自己的父亲,最终回到那个梦魇开始的地下室。眼镜的物理意义被放大了,不仅仅是主人公特点的设定,而成为了线索般的存在。
马里奥在地下室独白片段的影像呈现是华彩至极的。黛莉亚穿上母亲当年的衣服,仿佛被瞬间附体,眼神中透着幡然醒悟的坚毅。抬起头看到走廊尽头穿着大衣的男人走来,整个画面是虚焦的,观众知道,这是又回到了小黛莉亚的视线。需要注意的是,当年黛莉亚舔完店主给的奶油蛋糕后摘下了眼镜,之后发生的一切都在黛莉亚模糊的视线中发生,记忆在彼时被抹去了,而此刻又随着那坚毅的眼神找寻回来。母亲与自身的影像交替着,穿着大衣的男人一再靠近,摄影机终于找到了焦点,画面中露出了蛋糕店主的脸庞,并不是记忆中的卡塞塔。黛莉亚不禁抱头痛哭喊出了当年她的诬蔑之语。黛莉亚终于完成了和母亲之间的关系重构,才会在火车上说出阿玛利亚的名字,再也不是那个在画中的吉普赛女郎。
黛莉亚坐火车从那不勒斯回到博洛尼亚,母亲坐火车从那不勒斯去到博洛尼亚。这趟火车的终点是母亲生命的终结,同时母亲也用另一种方式在黛莉亚身上将生命得以延续,灵魂得以延申。
黛莉亚完成了对母亲、父亲和卡塞塔认知的倒置,也间接完成了在童年记忆中其他有关联的那不勒斯人的重新审视。尼采说:“没有事实,只有阐释,视角是所有生活的基本条件。”我们所有的感知、理解、思考和行为都是基于一个身份和视角的。对黛莉亚来说,身份和视角的转化成就了她的直面,诠释了她的变化。扩展开来说,在真实面前,我们都是高度近视患者,只能窥见大概的轮廓,却很难接近他人亦或是自己的内心深处。费兰特的文本结合马里奥的影像,成为了一种释然,对原生环境潜移默化影响力的释然。
在塔可夫斯基的自传体影片《镜子》中,将这种潜移默化表现为妻子与母亲的交叠,自我与儿子的交叠,用时间与空间的错乱性表达人一生对于原生环境的不可抽离,而这种不可抽离性是不被感知,不被言说的。黛莉亚最初的认知形成来源于过去的人和事,黛莉亚最终的认知变化也来源于对过去梦魇的直视,原生环境伴随着黛莉亚的一生,并无法摆脱,就这样被模糊地呈现着。
面对难以言说的真相,我们都成了近视眼,并永远将是。
读费兰特的书信集《碎片》,第一部分大部分收录的都是和《烦人的爱》这本书出版,获奖,电影改编等有关的书信来往内容。没读过原著和电影的话,真的有点读不下去。于是找了《烦人的爱》的电影资源(翻译为《肮脏的爱情》),几天前刚刚被弯弯字幕组翻译制作,他们发了个。感谢字幕组!
《碎片》里,费兰特的书信反复提及意大利女作家莫兰黛书中的一句话“没有任何人,包括母亲的裁缝会想到,母亲会有一具女性的身体。” 母亲的身体是被衣物包裹着的。
她说莫兰黛用男性第一人称写作时,是戴上了一张男性的面具”我感觉到这种伪装的目的就是通过文学,施行母亲的裁缝无法完成的工作:把母亲的形象从包裹里拯救出来。她利用青春期到成年的那段时光,让母亲本来的身材显露出来,讲述女性体验中没有讲述过的东西。”
而费兰特本人,或许也在尝试如此,打开千篇一律的潦草“包裹”,展现未被言说过的复杂女性感情。
视觉化的影像让这种改变来得更直接。
阿玛利娅自己就是裁缝,她给女儿做衣服,或许也给自己做衣服。老年的阿玛利娅第一次出现时,穿的是精致的酒红色裙子,不是莫兰黛描述的西西里母亲“永远都是黑色的,或者顶多是灰色或褐色”的衣服。
在镜头中,阿玛利娅的美一直延续到了老年。而她也总是在裸露。年轻时喂奶的饱满胸脯,被发现死亡时在海中漂浮的躯体,即使是松软膨胀的肚皮,也是一种对身材的“证实”。
酒醉的阿玛利娅身着鲜红的罩衫在篝火前舞蹈,甚至让我想到了《燃烧》里那个对着夕阳脱去上衣跳舞的年轻女孩。然后,母亲脱下罩衫,仅穿着胸罩,步入深海,篝火还在她的身后燃烧。
我们在电影里直观地看到母亲和女儿的躯体,看到年老而松弛的母亲穿上本要送给女儿的新内衣,看到身材姣好的女儿穿上母亲的旧西装,却都那么合身。小说的最后一句,是黛莉亚的独白“阿玛利娅存在过,我就是阿玛利娅”,在电影中,黛莉亚让车厢里的青年叫她“阿妈利娅”。
正如费兰特自己评价的,电影最震撼的,就是对于服装的运用。从一开始的淡绿色帅气男士西服套装,到后来那条所有街上的人都要看两眼的红裙子,再到最后母亲的深蓝色西装,服装的变化标志着剧情的推进和黛莉亚一步步接近真相的过程——母亲死亡的真相,童年的真相——直到她获得内心的和解。因为性感美丽的脸庞和躯体,阿玛利娅被身边的男性凝视,操控,羞辱,殴打,跟踪了一辈子,她也尝试逃离,可即便到了老年还要遭受威胁。母亲的死亡是否是一种解脱?黛莉亚早就离开了那不勒斯,选择了独身,但是因为母亲的死亡,她不得不回来直面和消化这一切,包括童年自己受过的侵害和犯下的错。然后她穿上母亲的衣服。费兰特写到 “对于黛莉亚来说,衣服是身体的表层,母亲的身体——最后终于穿上的身体,母亲死去的身体,可能正因为死去了,才会永远活在她心里,推动了她后来的成长和独立。”
期待原著的翻译和出版。
首先感谢弯弯字幕组!
重新再翻了下《碎片》(感谢陈英老师!),对于影片的理解倒是有更上一层楼,碎片里不仅有费兰特和导演讨论对剧本的修改,后面一篇《服装与身体》更是对导演很高的赞赏了,费兰特在其中提到的一些场景绝对是本片高潮的部分,例如一开始和母亲在电梯中的会面,只是女主一句“你一直有情人吧”开始奠定出母女关系中包含嫉妒、排斥的基调,如费兰特所说,“但是最有张力,最让人不安的是电梯里的场景:身体互相碰撞,吸引夹杂着排斥,母亲的肚子肿胀着,女儿的肚子很瘪,这个场景好像是在展示两个人的精神状态,而不是她们的身体。”其实从一开始母亲就无法理解女主为什么会喜欢一个人来到别的的楼层,只站在黑暗中的电梯里,而当女主厌恶又惊讶从母亲肚子上抽回手,让母亲离开时,母女关系的刻绘,从一个个肢体语言中表达出来,对观影者来说不得不是一剂猛药。
在之后的剧情中,女主继续探寻着母亲死前到底发生了什么,童年生活中出现中父亲,舅舅,卡塞塔,安东尼奥,这四个男人又重新出现在女主现在的生活中,而他们从一开始敌对状态转而变成了一种“惺惺相惜”甚至开始做交易的一种坚不可破的父权社会联盟,或者说从一开始,女性在他们的生活中就是一种可交易的附属品,“母亲的身体是“吉普赛女人”裸体的原型:父亲与卡塞塔之间的决裂(中间还卷入了阿玛利亚),起因是对那具身体以获利为目的的使用产生的矛盾。”父亲对卡塞塔的嫉妒和仇恨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与卡塞塔相比之下对于自身怀才不遇,贫穷,性方面的挫败感,可能一直以来,母亲在父亲和舅舅的眼中,就是男人间较劲的产品。而这种对母亲的贬低和唾弃则延续到了女主的身上,让她觉得自己的母亲确实做了很多不可告人的事情,是别人口中的“婊子”,对母亲身体萌发了敌意,母亲极具有诱惑力的表现成为了女主心中母亲的罪行。之后小时候的女主撒谎看到母亲和卡塞塔的婚外恋成为影片中一个链接点,在当时也成为了父亲等人的控制欲无法宣泄的出口,影片也借着成年女主的嘴质问出“可是当时你们为什么要相信我!”。
服装无疑是影片的另一个亮点,女主从出场就穿着着带有男性特征的服装,在穿上母亲送给她的红裙之后,好像从一个想要成为旁观者的社会来到了女性真实处境的世界。对于女主来说,衣服只是可穿上的表层,真正一直在追逐的,是母亲渐行渐远的影子,和已经死去的身体,在结尾处从地下室内穿上母亲的另一件蓝色套装,是母亲原来的身体,脱下的红裙,却并没有脱下和母亲的联系,最后她接受了与母亲的和解,在离开那不勒斯的火车上,她看到母亲在遥远的海滩,穿着红裙,在篝火前肆意的舞动,那一刻她才感到那是真正的母亲,从家庭中被解放,父权中被解救,具有真正自我的母亲。最后在火车上的一幕,女主往自己的身份证件上画上母亲老式的发型,开始二合一的形象,从女主的神情中看到了喜悦的成分,连最后被问及叫什么名字,都欣然说出了“阿玛利亚”,属于母亲的名字。看来从这混乱的那不勒斯逃离的,不仅是女主,也有母亲。
最后,期待能早日读到原著小说!
我知道猫狗没有自我(ego),所以看起来嫉妒是一种本能。
我的狗无法独处。它有严重的分离焦虑。一旦发现我出门不带它,它便立刻陷入一种焦躁——它挖洞、啃墙角、撕尿垫或者追自己的尾巴,它永不停止,它拆毁一切。
我的猫无法忍受我跟狗互动。它厌恶狗,炸毛、弓腰、嘶吼——它需要掌控,也企图占有,我不确定它是否期待我在它面前死掉,从而霸占我的身体和屋子里的一切。
黛莉亚对母亲有相似的本能反应,阿玛利亚看上去从没经历过黛莉亚的那些成长的烦恼,这一点尤其令人厌烦。影片一开始,阿玛利亚的首次登场便彰显了她的女性身份——她用女人的身体给孩子喂奶;在公交车上,她没有因为男性乘客的凝视而不安,甚至习以为常;穿过漆黑的桥洞时,她也没有共情女儿的眼泪。
 各种构图里,黛莉亚常常背对着阿玛利亚
各种构图里,黛莉亚常常背对着阿玛利亚黛莉亚不明白,在这座拥堵、嘈杂、粗鲁、没有边界的城市,用费兰特的话说,这里是“令人不安的那不勒斯和男权控制下的社会”,母亲为什么总是不必遵守那些显而易见的规则:她可以说走就走,不关水不锁门;可以对裁缝工作造成的手指伤势毫不在乎;可以在被邻居撞见情人时率先破口大骂。
在黛莉亚能够理解阿玛利亚之前,那是她唯一能参考的女性形象,她很容易认为女性本该如此。可是,如果阿玛利亚是女人,长得不像她、也无法过她那种生活的黛莉亚是什么?
《碎片》里,费兰特提到一段因为过于直白揭露黛莉亚的内心而删掉的段落:
我的头发很细,跟我父亲一样。我的头发又细又软,看起来不蓬松,也没有光泽,它们随便披散在头上,很不听话,我非常痛恨我的头发。我也没办法把头发梳成像我妈妈那样,挽成一个发髻,额头上有一个波浪,几撮最不听话的小发卷会出现在眉毛上。我看着镜中的自己,非常生气。阿玛利亚真的很邪恶,她希望我永远不要像她一样美丽,她没有把她的头发遗传给我,她的头发又好又旺...
 黛莉亚最终给自己画上了母亲般的头发
黛莉亚最终给自己画上了母亲般的头发那是一种孩子独有的足以吞没自身的嫉妒。在这样的本能之下,十二岁的黛莉亚把自我厌恶归结于头发,就像她把整座城市的厌女归结于阿玛利亚。
“I was no I”,作为费兰特早期作品的重要特征,黛莉亚也是一位具有模糊身份的叙述者。失去了来自母亲的那部分自己(ego)之后,她进入一种失衡的状态——她看见男性主宰的世界,认为世界本该如此;又看见母亲代表的女性示范,认为女性本该这般;二者互相撕裂,又与自己如此相关。
《碎片》里,费兰特提到一个原本被加在小说里的梦境,呈现了这种撕裂:
我我要在一个男人面前脱去衣服。我不想在他的面前脱衣服,但他就赖在那里不走,他饶有兴趣的看着我,等着我。这时候,我小心翼翼地开始脱衣服,但衣服一直脱不下来,就好像是画在我身上一样。那个男人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我很愤怒,我感到一种强烈的醋意,我感觉他有别的女人。
我想奋力留住他,我要夺回他,我用两只手抓住胸口,想撕开我的身体,就好像那是一件睡衣。我感觉不到疼痛,我只是发现,在我的内部有一个活生生的女人,我只是另一个女人——一个陌生女人的裙子。
我无法容忍这件事情,我的醋意在上升。后来我醋意大发,我嫉妒我身体里的女人,我想抓住她,攻击她,杀死她。但我们之间有一段无法逾越的距离,我根本触及不到她,那个男人的笑声在继续,那是一种无法抑制的笑声。我再看着眼前,那个男人已经消失了,是我母亲在那里,我感觉她从开始就在那里。
母亲离开后,黛莉亚不必继续活在母亲身为女性的阴影之下,但同时她也失去了对此前埋葬于地下的记忆的庇护——她无法将城市的不公迁怒于其他人了。
现在,如果她想重新找回自我(ego),她需要脱下男性化的服饰,需要理解母亲如何不需要衣服的庇护去直面一切,包括死亡。
比起几次穿上母亲衣物的场景,另一处值得关注的场景是温泉。费兰特在给导演的回信里解读黛莉亚和安东尼奥在温泉的场景,“黛莉亚的身体无法突破一种状态,她和母亲性感的女性形象截然相反...这个场景呈现她身体的欲望和厌恶,她作为女人的痛苦。”
阿玛利亚最后的生命也是漂浮在水面上的。如果说地下是被篡改的童年,高处的电梯是青春的庇护所,水面则事关赤裸的生命本身。地下室穿上母亲的外套更像是仪式的完成,而温泉内场景的转移——从被动到主动,光影从阴郁到明亮——是真正“成为自己”的开始。


正是在那之后,黛莉亚开始重新接纳自己的女性身份,她把樱桃当作耳饰,她独自乘车,独自面对父亲......
波伏瓦说,做(being)自己并不意味着从出生到死亡做同一个自己,而是以一种不可逆转的方式“成为(becoming)”自己的过程。《八月处子》便着重呈现女性“成为自己”的过程,一个相似的场景是女主角伊娃原本在泳衣外披着红色外套(近乎张扬的性别隐喻),随着被友人捉弄地抛入水中,她干脆脱去外套,自在地漂浮于水面之上,她仰面自语,“成为我们自己”。

伊娃通过探索月经与自然的关系理解自身,即通过向内的方式孕育自我(在第一次主动和陌生男性发生关系时,她喃喃自语“我想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怀孕了”);与之不同,身处男权笼罩的那不勒斯,黛莉亚需要借助母亲的衣服实现这种“becoming”的过程,她需要一种温和的方式与过去和解,更需要让过去的经历成为一种力量——像费兰特自己最满意的小说最后一句,“阿玛利亚存在过,我就是阿玛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