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层社会 Les amants(2011)

又名: Low Life
编剧: Elisabeth Perceval 尼科拉·克洛茨
主演: 吕克·切塞尔 Michael Evans 埃莱娜·菲利埃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法国
上映日期: 2011-08-08(瑞士)
片长: 120分钟 IMDb: tt1784515 豆瓣评分:0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演员:
影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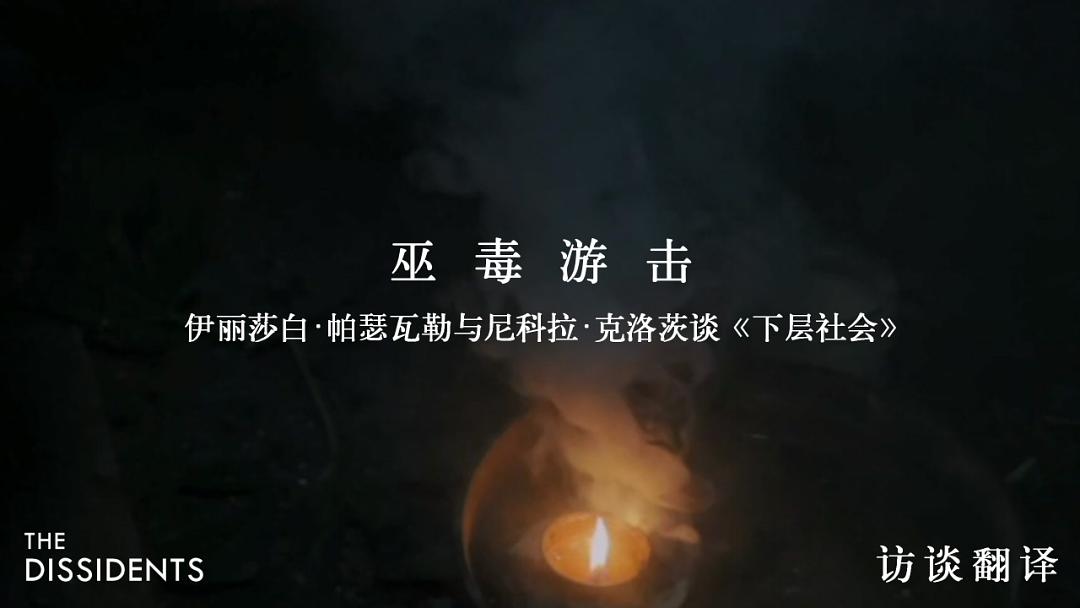
原标题:Guérilla vaudou 采访者:Mathilde Girard / Frédéric Neyrat 受访者:Nicolas Klotz / Elisabeth Perceval 翻译: 原文地址:
全文约18000字 阅读需要38分钟
电影的边缘
弗雷德里克·内拉特(下称FN):我们先来谈谈:电影,尤其是你们的电影,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娱乐产业中处于什么位置?换句话说,如今以谁为敌?
伊丽莎白·帕瑟瓦勒(下称EP):这很有趣,因为昨天早上我刚对尼科拉说......你还记得吗?
尼科拉·克洛茨(下称NK):是的,我问伊丽莎白我们在当代法国电影中处于什么位置,她说这就像一种变幻莫测的爱……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美。
EP:不确定性就是如此,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空间,同时不可能性也像灰烬下的火苗一般藏匿其中,在不可预见的地方会有新的事物发生。我真切地感受到,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一处被称为“边缘”的自由地带。我的意思是说,它既是一个我们远离外界骚动的“秘密花园”,又是一所“难民营”,在那里我们发现自己在市场支配下被拒之门外并被驱逐……在毫无安全感或舒适感的边缘进行创作,使我们的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活陷入不确定性、危害和风险之中;这些感觉非常接近于爱中的感觉。我们总是凭依一路走来领会到的东西进行工作——凭遭遇、朋友、地方、周围的人、书籍。通过多年来收集的事物,我们一点一滴地构建了自己的作品。不过我们的方法当然会遭到很多拒绝和不信任。这个行业需要控制,需要计划,需要去寻找“零风险”的安全感——这让我想起了Meetic网站上的广告,“爱无风险,Meetic,不惜一切代价保证爱的安全”,这是同样的一个世界,所有这一切……这是一个持续时间的过程;我们显然远离了那些数理性的痴迷,远离了既定的规范,电影工业,就像所有的市场一样,去寻找最小的风险,寻找并不存在风险之处,至少资金支持者是这样的。我们可见,这个保障我们所有人都安全的自由世界如今是如何威胁到爱之感觉以及创造力的。爱和电影一样,毫无可能在风险缺席的情况下存在。它无法避免偶然性。爱、电影——它们是生活,它由无数的遭遇组成,总是遍布着偶然性。电影是一场充满智慧与爱的冒险......我们拍摄电影,试图重构一个时代的某些事物,某些正在进行中的东西。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并不总是能够知道。几个月来,这是一项地下的、一丝不苟的创作突然间占据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当我们开始制作一部电影时,我们就知道,我们将经历三四年之久的战斗。你必须如此;我想说的是,电影是忍耐力的产物,电影的存在离不开立场,离不开在各种意义上忠实于自己的立场:例如美学和政治领域相关的选择,还有你与演员、与摄制组、与摄影机的立场等等……就像在生活中一样,在电影中采取立场会使我们孤立无援,使我们被迫退守,尤其是,当这些立场是不明智甚至往往激进的时候。因此,我想说,我们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是孤立的,是被抛向边缘的电影……但今天,边缘的人并无法团头聚面。我们孤立无援,各守一隅。我们因愤怒——因为有感情、诗歌、友谊、爱情,因为它们想让我们相信,这一切都不再有意义。他们想让我们相信,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
NK:在《下层社会》(Low Life, 2011)的制作过程中,我们遇到的资金方面的问题,在这点上,可以说代表了电影行业的——就是Canal+ [1];他们很快就加入了这部电影的制作。电影业为我们打开了第一扇门,给了我们生存的机会。我们注意到的是,当由《人性问题》(La Question Humaine, 2007)打开的大门关闭时:L'Avance sur Recettes [2] 和la Région Ile de France,这其实并不属于电影工业,他们更像是同行——电影制作者、制片人……因此,在这部影片制作中,困难是这样来的……
FN:有没有朋友呢?
NK:在法国电影界中?……“哦,我的朋友们,没有朋友了!”如今,法国电影人之间已经没有真正的友谊了,这是一种可怖的败落。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从电影制作人到影评人,每个人都会受到这种败落的影响,而新的电影制作人也必须与这种败落作斗争,以达到新的电影境界。前几天我看了加瑞尔的《艺术部门》(Les ministères de l'art, 1988)。厄斯塔什讲述了戈达尔如何帮助他拍摄《蓝眼睛的圣诞老人》(Le père Noël a les yeux bleus, 1966),以及他为完成这部影片所支付的费用。这部影片是《男性,女性》(Masculin féminin, 1966)的失败版本。加瑞尔真正在过去和当下的电影之间找到了自身;他是一位出色的纪录片导演。在《艺术部门》中,您可以看到加瑞尔、厄斯塔什、阿克曼、杜瓦隆和施罗德之间的循环友谊。你可以从镜头中、从他们的声音中、从他们的交流中、从他们谈及的困难中看到这一点。这些电影人济济一堂,你会觉得加瑞尔为自己和其他同行都注入了活力。与雅克和泰希内在一起则要冷清得多。与他们在一起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一种最为基础的共识。你可以感受到那些希望融入体制的电影人与那些置身事外的电影人之间的隔阂。在《她在阳光下度过的岁月》(Elle a passé tant d'heures sous les sunlights, 1985)中,曾被问及如何拍摄儿子的加瑞尔向杜瓦隆发问,他是如何在《哭泣的女人》(La femme qui pleure, 1979)中拍摄女儿的。他们的对话令人难以置信。电影制作人之间,既是儿子又是父亲,既是工匠又是艺术家——他们之间有着致密的联系。“电影之死”也是电影人之间的友谊之死。我对此丝毫不怀旧,我只是觉得有一种我不知如何应对的庞然混乱。
 Elle a passé tant d'heures sous les sunlights (1985)
Elle a passé tant d'heures sous les sunlights (1985)EP:就像和平时期的所有军队一样,电影也是分门别类的,戈达尔在谈论手册时期时如是说。我不知道在这个和平年代是否依然如此,因为如今我们生活在接连持续的战争中。经济、金融,与一场肮脏不堪的战争同样致命。无论如何,我们会发现,那些对这个系统驾轻就熟者将会成为财政援助委员会、各种小组和项目遴选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深谙如何捍卫自己的领地,并毫不犹豫地将资金从他们认为伤脑筋的影片、那些不属于他们亲密宗族的影片中转移出去。我们项目的小组委员会反馈给我们的参考框架展示了我们与富有、现代和共识化的电影之间存在着的巨大鸿沟。那些自称为左派的电影人总是受到持这种立场的电影人的批评……“你们是左人”,这已经成为一种最高的侮辱,我们对他们这种咄咄逼人的方式感到震惊,以至于“左派”最终听起来像“恐怖分子”。金钱既已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投资者、锁链和剥削者主要追求的是行之有效的 “文化”产品,正因为如此,他们需要的是遵守既定商业规则的电影。这还有什么余地去对审美、政治、艺术或思想作出真正的质疑呢?说到这里,我看到了自己某种意义上的天真;人们不在乎,市场逻辑亦然……这是一场数字战争,通过这场战争,我们不得不服从于学习到的的审美观以及市场营销;今天,文化物品的节奏有一种潜在的规则,在电影中更是如此,就像交通、食物、性关系、教学中的那样……导向狂热的上升,一种对速度的需求,作为面向空虚逃避痛苦的方式……死寂时代的恐怖,对快速连接的需求,这一切都是幻觉,是谎言,是对我们感知力的集体性麻醉。我们并不是唯一必须面对这种问题的人,我们必须思考我们可以抵御其中哪些条件,以便在不被贴上一致性标签的情况下为电影赋予生命。要想继续拍摄我们的电影,唯一的办法就是像移民一样在国家外部创作,填补这个类似于“下层社会”的空间。这就是我们试图与最亲密的合作者共同进行的所作所为。我们试图与哲学家、作家朋友建立一个合作交流的网络……我们试图发展合作的方式,不仅仅是创作,还包括联系、关系、交流,这种欲望已变得真正具有生产性。其生产就是生命本身。
NK:是的,我们该如何合作?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今,很多电影人都陷入了品牌和圣像的逻辑之中。我这不是评判,仅仅是评论,是客观的陈述。这是苏联电影的资本主义版本。为了给电影融资,电影制作者必须传达一个资本主义想要或可能想要的、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陈述。一个人必须是它的一部分,并且相信它。甚至一个人的反应方式也必须参与其中,以让资本主义变得更性感、更年轻、更现代、更引人之欲望。把《大都会》(Métropolis, 1927)变成一次艺术之旅。这是一种全球性的变异,显然不仅仅与电影有关,它还扩散了一种观念,即我们将从历史中脱颖而出,因此也将从电影史中脱颖而出。继续说到厄斯塔什,在厄斯塔什自杀后,让-皮埃尔·利奥德在《蓝眼睛的圣诞老人》中的连帽大衣与他一同入土为安。柏林墙的倒塌、数字革命……厄斯塔什说,他无法空腹去想马克思。这是具体而残酷的。电影的驱力是历史,而非为了让人们相信世界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制造的艺术之旅而资助的拜物教图像集合。对这次旅行的资助金是由旅行本身构成的,并产生了大量的连接、网络和成瘾迹象。问题在于欲望,它是一剂烈性药物。资本主义为了夸耀自身的荣光,并使其统治方式、警察系统和技术仪式合法化,出现了一系列致幻产物。作为一名艺术家,你怎能同意参与其中呢?同时,你又怎能不同意参与其中呢?这个系统的网络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几乎毫无可能摆脱它。要制作一部电影,就必须在美学和政治领域上与他人抗衡。由于疲惫不堪,许多电影人放弃了这些问题——欧洲将成为一次冷酷之旅,ARTE France Cinéma 的年轻小读者们将收到 iPad 来阅读流水线上的剧本。与此同时,希腊和西班牙的年轻人在过去几天里冲上街头,因为他们在这个极端僵化和掠夺性的欧洲感到窒息,认为没有未来。在这个欧洲,他们要挫败凡人之青春以为富人提供永恒的青春。
 Le père Noël a les yeux bleus (1966)
Le père Noël a les yeux bleus (1966)EP:小组委员会的读者在他们给《下层社会》开头的场景和对话加的注释中写道:“年轻人不会那么说话,他们现在不会那么思考……”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被排斥的人》(paria, 2001)中,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创伤》(La Blessure, 2005)中的非裔身上,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人性问题》中的镜头中。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存在着一种表象的电影,一种作为增殖的电影——它在脱离现实的、可悲的外部模拟中进行效仿和复制。就言语而言,我们听到的是心理及其戏剧效果,是预制的、粗糙的感情表达。这是一种并不自然的自然主义,只不过是一套惯例,这种机动的增殖停留在表面。因为你必须一成不变地再现人们所期待看到的东西,诸如青春、镜头、流浪汉和移民……它转向一种以条件作用取代经验的痛苦。拒绝这些谎言至关重要。看电影是一种审美体验。这是第一次看到与感知事物,在此我们有可能看到并理解整个世界。我们说这种自然主义,这种著名的自然,与现实主义对垒。真实从来都不是既定的,真实是被实现出来的。我们与非专业喜剧演员或出演这些影片的非常年轻的演员一同工作一年或两年之久。我们必须首先讨论我们所知的、与我们相一致的、与我们自己的感知力和故事相切近的东西。要对真实事物的关系持有最基本的疑虑。而电影存在于真实和虚拟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正如戈达尔所说:“现实主义从来都不是完全的真实,而电影的真实则必须经过修饰。” [3]
 Low Life (2011)
Low Life (2011)NK:让我们采用一个有趣的词:fétiche(拜物教),这是白人对他们在殖民探索过程中发现的原始人物品崇拜的称呼。另指迷信者认为具有神秘力量的人,并毫无疑问地受到崇拜。在精神分析中,fétiche 则是恋物癖者的淫欲对象。它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力量——殖民、迷信、统治、占据和性变态——的交汇点。巫术(Sorcellerie)。生命政治的力量通过这种从古老的统治关系中提炼出来的白色的、技术和色欲的魔法传递。这是一种占有了他人的纯粹权力意志,作为电影制作人,要想生存下去,要想参与规模庞大的黑色资本主义群(masse capitaliste noire),作者就像所有旅行中的物件——也必须像恋物者那样进行流通。由于他们自己的影像,他们自身也成为了魔力的形象。它们进入了欲望经济,与资助殖民主义野心之旅的金钱结为一体。有必要再看一遍安东尼奥尼的《扎布里斯基角》(Zabriskie Point, 1970)。他对这一切早有预料,也有点像布列松的《很可能是魔鬼》(Le diable probablement, 1977)。白领法西斯主义、警察控制、青年、消费之旅、平克弗洛伊德的音乐。如今,这种旅行是如此强大,它让你的思想、你的身体、所有的边界都爆破开来。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世界。很明显,我们今天所知的世界太小,太陈腐,无法应对这场革命。这是一个完全爆炸性的局面,其持续时间将与旅行的诱惑力生效时期一样长。让我们扩展边界,与社会建立新的关系,与历史、艺术、哲学、友谊、爱情、政治建立新的关系……让我们击溃这些强化边界背后的壁垒,并试图瘫痪特权阶层。这就是内战。
 Le diable probablement (1977)
Le diable probablement (1977)玛蒂尔德·吉拉德(下称MG):你们的身份是异邦人,或者说与法国电影有隔阂?
NK: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我对法国电影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就法国电影史而言,我们和许多法国电影人一样,是维果、雷诺阿、布列松、戈达尔、鲁什、厄斯塔什、加瑞尔等人的继承者。在某些意义上,我觉得自己很接近戴普勒尚及其浪漫主义野心。比如《哨兵》(La sentinelle, 1992),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杜蒙的《哈德维希》(Hadewijch, 2009)。这是两位真正懂得如何在法国体系的中核心创造独立性的电影人,他们与制片人之间的故事也很精彩。我极力证明,我们属于法国电影,却不知道自己在其中占据什么位置。这不由我们说了算。也许这就是一个变异之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电影的融资方式确实有点像阿根廷、葡萄牙、加泰罗尼亚或泰国电影。十年前,影评人称这些电影为“贫民电影(mauvais film)”——联系到“富有电影”或“中间电影”。即使这些分类已成为现实,我也不再愿意以这种方式来看待法国电影。它太僵化、太瘫痪、太陈腐而囚困在预测中了。我试图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它。或许,在国际化未来以及与其他电影人、和新一代的合作方面,美学和政治问题将得到巩固。我试图更多地从断裂和意外的角度去思考。就像如今一切有意义的事物一样,一部电影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它可能会抵达未知之处或其他地方,它可能会侵入。的确,这变得相当容易,因为法国电影体系的资金过于富足以至于能够自洽,不再需要局外人来出口他们的产物。无论如何,除了销售和地域之外再也不需要任何局外人了。我们用自己的资金拍摄了《人类问题》,采用超16毫米胶片,其预算比法国电影的基本标准低50%,聘请了几代法国本土演员。迈克尔·朗斯代尔、琼-皮尔里·卡尔弗恩、爱迪丝·斯考博和洛乌·卡斯特尔等演员,他们是电影史的一部分。马蒂厄·阿马立克和瓦莱丽·德维尔曾出演《哨兵》尼古拉·莫里、利蒂西亚·斯皮加雷利(Laetitia Spigarelli)和德芙妮·楚里奥特,他们都是充满激情的年轻演员。影片效果很好,在二十多个国家销售。效果如此之好,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为此开销。
 La Question Humaine (2007)
La Question Humaine (2007)EP:这个故事不是来自于我们,而是我们的朋友所讲述的,他们并不了解我们在为《下层社会》出资时遇到的巨大困难。现在我们被迫在经济上做出些贡献,这些我就什么都不了解了。《人性问题》的制作预算很低,但在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制作这种野心勃勃的影片的可能性。虽然在题材上存在一些问题,那是另一回事,但以130万的资金拍摄《人类问题》这样的影片,它将某种功能性理论应用到了电影中,尽管我们知道许多电影都有其昂贵的一面。用少量的预算拍摄野心勃勃的影片,这对于开创另一种电影经济是很有诱惑力的,而且可以证明其可行性;它给电影体系带来了压力。我们对此深有体会。此外,我们还制作电影是也为影院做了打算。《人性问题》售出了15万个座位,这部电影找到了它的受众观者,至少它比一般的独立电影卖出了更多的座位。但危险正在于此!观众不应该自寻烦恼!玛格丽特·杜拉斯说过:“对于专业电影人,也就是对立于电影作者的电影复制者而言,我们是夺走‘他们’钱的不法之徒。而这一万名观众的边缘,是大多数逆流而上、忠于自己电影的量化电影制作者永远也无法拥有的。这就是他们厌恶我们的原因。尽管他们卖出了数百万张票,但他们却想夺走我们的一万名观众。”[4] 在《人性问题》取得成功之后,我们希望下一部电影的融资过程会简化一些。但实际上,我们无法避免被问题淹没。三年的等待、开会解释、更多的等待,然后重复我们所做的解释。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费尽心思凑出两份钱,这两份钱足以支付一个新兴国家的电影预算,但还要加上片酬、寻找材料、装饰、传输、富裕国家的制作费等所有相关成本。原本为数不多的几扇被打开的大门现在却在我们面前猛然闭锁。我们说我们很固执,这必定是一种责备……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这样想。坚韧,正如人们对爱情的称说,这是一场坚韧的冒险。不放弃,知道每部电影从构思到完成都是一个真正的挑战。这是一个奇迹。我们还有多长时间?只要有反叛之风在吹拂……
FN:因为这不会花销太多!就好像问题不在于电影需要多少资金——无论如何,这对电影来说都是非常富足的——而在于对电影工业本身有利可图的融资……但让我们回到“身为异邦(être étranger)”或“局外人”的问题上来。尼科拉,从什么意义上说,《下层社会》最终是一部允许为您所说的那种自洽关系作斗争的电影?
NK:“斗争”这个词不对。我们无法与之斗争。你如何与一场已经发生的灾难作斗争?我们必须在工作中很好地组织我们自身,以便带着新的力量回归。我相信,这都是好电影自己的事。这就是为什么“第一部电影”往往如此具有创新性。它们是在不经意间出现的。赋予电影力量,真正的力量、其独特亲和力和集体性力量的,是决策者为了控制电影而将其排除在外的东西。这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它像声波一样传播,完全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并在社会中作为一位启示者。《下层社会》是一部如此充满希望的电影。
MG:是的,这让我觉得,在您的每部电影都有必要让电影成为被拒斥之观众的庇护所。就好像你所意识到的这种边缘化,恰恰是对你所从属的主体之暴力的精确责任追究。资本主义开启了两个社群、两个场景之间的交流,以便召唤出我们可以在“异质存在(existences hétérogènes)”和“电影”的标题下集结而来的东西。我认为,德勒兹在谈到“失败者(Peuple que manqué)”,以及电影如何负责将存在转译并赋予其形式时,所理解的就是如此。
EP:当然。关于创作者被抛弃以及被拒斥在他们的职业之外的问题每天发生在我们眼前,并让我们更接近那些被拒斥、被边缘化、被孤立者……很多移民、非裔、巴勒斯坦人、阿富汗人和摩洛哥人发现自己身处的环境,尤其是在法国,让他们感觉毫不亲和。我们并不缺乏与这类人接触的机会,这样而来就产生了联系和友谊,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和希望。正如我们所说,我们在生活中、在社会中通过选择性的亲和力找到我们的拍摄对象,但如果这些邂逅不类同于个人情感、生活经历或愤怒,就不可能成为电影。
NK:在《下层社会》中,侯赛因这个角色是一个难民,他在大学学习,会说法语,是一个知识分子而非体力劳动者。他是一个年轻的阿富汗人,在某一特定时刻,他则可能是一个非法移民,而这不一定与体力劳动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当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们希望拓宽视野,打开局面,而不仅仅是将侯赛因置于一个被剥削的未来——就像《创伤》中的英雄们一样,他们靠着这种不上台面的工作生存了下来……侯赛因从全球化的另一个角度向我们讲述了这个故事。在这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轻人能够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一同工作。他与卡门和她的朋友们参加同样的聚会,读同样的大学,但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东西,让他与其他人相比处于例外状态。他需要证件,这也是他公开宣称希望成为社群一员的原因。但这也是他失去做人权利的原因,并迫使他变成了一个恶魔机器,最终腐蚀了所有与他有关联的人。爱上侯赛因就等于加入了他与这台机器的斗争,从而产生恐惧、偏执、倦惫和绝望。卡门与他分享的那种激情很快让她陷入了一种偏执,而这种偏执就像是一种宿命。受到攻击的是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本身,并由此影响到整个社群。我很喜欢我的朋友桑蒂亚戈·菲洛尔(Santiago Fillol)的说法,他说法国国权(Etat)在卡门的床单上滑落了。那里有些东西在玩诅咒。豁免状态(l'état de l'exemption)是一种咒语,因此才如此强大。其他人物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比如年轻的哈蒂安·胡里奥在地铁里被捕,被送往医院检查骨骼。当医生告诉他,他的真实骨骼年龄与证件上显示的不符时,他变得嗜睡。这件事让他彻头彻尾地疯了。在它占据(possession)身体的过程中,医疗-法律技术催生了行政和司法的咒语。影片对这个词的假想有两种意义上的奇妙:巫毒教(vaudou)是一种积极抵抗警察国家的形式,我们将其解释为被诅咒的国家。影片的主题是寻找抗衡行政诅咒的阴谋方式:向警察施咒,同时抵御他们的诅咒。我们逐渐成为内战的一分子,成为抗衡警察的巫毒游击队。《下层社会》是一部如此奇妙的电影。
 Low Life (2011)
Low Life (2011)爱情与政治的状态
FN:在影片结尾,当三人找到彼此时,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国权和浪漫关系就变得很有趣了。爱是一个抵抗之处,但也是一个引入国权之处。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个生命政治的场所,在这里各种力量相互碰撞。您是否认为爱在当今政治中占中心地位?如果是,是以何种方式?
EP:是的,我认为应该拯救爱的状态。爱应该被捍卫,因为它受到了全方位的威胁。爱的某些方面正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当今我们相信对身体的占据、一种单数的占用,一切都只是为了维持外观。这是一种俘虏,其中我们的思考、感觉和看的生产能力都受到了影响和打击。从国家从床单上滑落的那一刻起,它也滑落到注定会出错的感觉上。爱已经被击倒了;我们必须站起来,不要表现得仿佛感情一直在那里,一成不变…..爱的参与必然是一场反资本主义的战争,因为它并非资本化的。爱是不可化约为法则的。戏剧、电影和文学常常被视为爱的反社会性。“世上有情人从未孤身。”爱的感觉是被重塑并崭新呈示的——在爱本身和其他事物重塑的过程中;机会、未知,这就是事情出错的地方。同样,当爱情因我们否认其重要性这一事实而受到威胁时,我们就开始抵抗入侵者,成为抗击爱的战斗者。自由主义的观点看来,爱是一种无功用的风险。爱孕育了存在,就像一种集体性的热情,几乎赋予了整个世界以强度和意义。我们怎能不看到爱情与政治之间的共鸣?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一种永远无法放弃的信念。暗地里,爱的动力是对世界变革的不断呼唤,是对创造世界的报告的改变。这种迫切的愿望明确表达了一场剧变的需求,但这种剧变不是在形式、话语、意识形态或政党之下的。今天那些二十余岁的人,那些《下层社会》中的恋人们,怀着全部的欲望投入到生活中的人,不能对自己说一切都已成定局,他们不能。他们知道有一种诅咒,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恶魔般的诅咒。它很可能是魔鬼。
 Low Life (2011)
Low Life (2011)MG:难道我们不能认为,在这个社群遭受苦难之处,在爱的感觉遭受打击之处,电影可以成为发明和重塑那些感觉似乎无法产生的爱和政治的空间吗?影片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那就是您的作品遍布矛盾。当您对弗雷德里克说爱是一个卓越的生命政治场所时,这也意味着这对爱侣可以被分离。在卡门和侯赛因的关系中,有一些被迫为社会所拒斥,并希望找到一个对手的东西。或然是恋人的社会变得极权,只有女人才能通过监禁男人以拯救她的虚荣之爱。这是影片中一个极为感性的时刻。侯赛因的离开拯救了这个社群的某些东西,因为爱情的情状同时也是一个抵抗的地方,也是可以转变为隐遁的东西。将爱作为一种政治情感,就意味着在爱中,可能叛离社群的东西将不会得到拯救。
EP:卡门和侯赛因并非打算排斥自己,而是希望找到一个保护自己的空间。是社会(société)在追捕他们,甚至追捕逼迫到了他们的床上……卡门爱上了一个非法移民,这让她陷入了战斗,是社群发现了他们之间的纠葛。这对爱侣随后又被卷入了政治中,因为他们的朋友必须自我定位,自我组织。他们必须学习课程并给侯赛因带书,因为他无法继续读大学了。同时,他们还必须建立联系,为他逃往另一个城市做好准备。有些人将被留下,或者不得不离开公寓,因为形势已经变得不可能了。警察在外边车内对公寓进行监听,他们的出现让公寓里的人变得完全疑神疑鬼。卡门发现自己只能像生活在战乱国家的人们一样过着隐秘的生活。当她发现自己的爱人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命运时,这对爱侣除却继续隐遁在公寓里别无选择。最终,卡门再也无法离开公寓,不知不觉中,一种莫名的占有欲占据了她。为了保护他们彼此的激情,卡门要“绑架”她的爱人,因为社会否决他们的爱情。一天晚上,这对恋人因为害怕警察闯入,用衣柜堵住了房间的入口。侯赛因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禁闭。一天下午,他决定前往大学,但卡门反对并禁止他离开。她出于本能,就像被追赶的动物一样躲藏起来,以保自己免受追捕者的伤害。在此他们试图找回被侵犯的亲密关系。对他们来说,“占据”并不是一种因策略而产生的心理感受,而是一种身体性感受,就像寒冷和灼热完全吞噬一个人。这对他和她来说都是一种冲击。侯赛因明白,卡门和他藏在一起是为了监视他。一方面,社会禁止这个惹人爱慕与渴望的肉体存在,另一方面,卡门无法忍受她的爱人被逮捕并驱逐出境。这是一场噩梦,侯赛因想要摆脱这段关系,他们争吵,他在寻找出路:“欧洲有一种被围困的思想状态,愤世嫉俗者被动员以对抗一种威胁,但究竟是哪种威胁呢?是对世界末日的思考,他们不想看到它,即便它就近在眼前,但旧世界早已被抹除。”卡门说:“我生活在追猎之中,但我无法逃脱……我需要打开自己、孵化自己”……但这并不是冒着丧失生命的危险。也许吧,但这并非鲜活的,这并非一条生命,侯赛因回答道。法则强加给他们的这种“身份”逻辑,甚至于让恋爱关系变成了犯罪。卡门被审讯官传唤到警局。她就像现代的安提戈涅,面对警察的攻击和谴责。她为自己辩护;我们不能要求一个爱着男人的女人谴责他或将他抛之于街道。她引用了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原则:“我违反了法律,但其目的是高于法律,因此我不会遭受谴责”……在此期间,侯赛因逃跑了。他不想让他的斗争影响到卡门。他说他是为爱而离开的。显然,他的行为更为复杂,我认为他无法忍受像小偷一样被关起来的生活,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冒着曾经离开阿富汗的那种风险,另外必定还有野心。爱作为礼物而来,而荒谬的法律却将它变作一场噩梦。他对此再也无法忍受。
 Low Life (2011)
Low Life (2011)NK:卡门,就像饰演卡门的卡蜜尔(Camille)一样,总是在青春期和成年期之间徘徊。我想拍摄她的突然转变,把她拍成一个突变者(mutant)。侯赛因给她刮剃耻毛的场景,一个“非法移民”给她刮剃耻毛的事实……
EP:这是一种习俗……将来的的新娘要剃光耻毛。这是在女人之间完成的的仪式。侯赛因自然而然地违反了这一习俗。他的举动表达了对于希望与卡门保持长久浪漫关系的欲望。在某种意义上,他已与她成婚。
Low Life (2011)NK:这也是法国人走进这个世界的地方!一个年轻女子将自己献给一个外来者的剃刀,这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这个场景与胡里奥的行政角色有关。骨质测试结果附有一份《法兰西共和国》印件正被非裔在占地者的房屋院落里焚烧。这是两个非常具有挑衅性的画面,同时也是戏法仪式。我想拍摄卡门在侯赛因和查尔斯眼前突变的过程。侯赛因和查尔斯看向她的时候,她的脸已不再是原先的样貌。
 Low Life (2011)
Low Life (2011)EP:查尔斯恰恰没有被占据。他看到的是爱、失落和遗弃的神奇状态,以及引发这些深沉忧郁情感的所有危险。他会对卡门说:“我很想找到你,现在我已经失去了你……”他继续为爱而争斗,忠于自己的承诺,忠于对她的爱,这是一种英雄主义。查尔斯是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也是福岛事故后的一代人。他对世界的参悟不是浪漫或灾难性混乱的结果,而是他用不可逆转的损害来衡量的灾难性现实之一。他觉得一切都将坠入地狱,人类正在深渊中起舞,而处于底层的人类可能除了毁灭别无念想。重大核事故的风险在统计学上是确定无疑的,也是一种撒旦式的现实。正是在感知当下的晦暗时,人们才会发现无形光明,才会获得应对当下黑暗的能力。对查尔斯而言,唯一还有可能被拯救的思想就是爱本身。他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否则爱将不复存在。他的承诺是完全的,因为未来将是爱,否则根本不会有爱……
 Low Life (2011)
Low Life (2011)NK:你这么说,我就想到了牺牲的问题。
EP:确实如此;查尔斯向自己发问是否应该做出自我牺牲以拯救其他东西。但他不会这么做;他拒绝把死亡带给自己。他决定不去死,就在那里,他牺牲了自己。牺牲是为了在一个拒绝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一切的病态世界中维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人成了流浪者,没有一个值得返回的国家。我们失去了诞生之国。但查尔斯强烈地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反抗,起源永远存在而且将会反抗。查尔斯说,反抗是值得的;绘画、写作、舞蹈、做音乐……为了重新发现艺术中失去的,我不再相信其他任何东西……一个可以记住这种亏蚀的空间……没有人寿保险,没有退休,没有被组织的旅行……他是正确的,你觉得呢?他不再相信自己的学业,社会已令他厌恶不堪以至于再也不想参与其中。他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MG:这也让我想到了发生在恋人卧室里的另一件事,那就是睡眠的回归。同样,爱是社群中的一处,睡眠也是一个社群空间,它围绕着胡里奥这个角色……
EP:这是一个社群空间,不仅有人类,还有动物、树木、自然、河流……
 Low Life (2011)
Low Life (2011)MG:这种睡眠也是一种反抗。在《创伤》和《下层社会》之间,我们可以看到警察制造了可以穿透身体内部的新型武器,而睡眠似乎是逃避这种监视的一种方式,一种保留自己的存在且规避剥削的方式。
EP:在监控摄像头、雷达、警察和他们所有的新型技术武器库之间,人类出于本能总会寻找逃避这种劫掠性目光的方法。在学校里,他们挑出可能有不良行为的孩子——他们在操场、走廊、卫生间逐一安装监控摄像头,他们在火车上抓捕无票人员,他们向和平抗议者发射橡胶弹——警察通过他们在街上和地铁里的出现控制着人类。我们的城市被清理了一部分居民——穷人被运走,疏散到郊区,一边是强者,一边是穷人。被剥削者和剥削者,被控制者和控制者,正如他们所说:“现在的混蛋是真诚的,他们相信欧洲”……我们的电影带有这种暴虐的痕迹。在《下层社会》中,警察处于一种隐蔽失眠的状态,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弥漫着监视的毒性副作用,那是一个可怖的警察社会。说到底,我们的国家不再控制这场经济战。为了阻挡审讯者的目光,“睡眠模式”成为一种逃避方式。《下层社会》中的人物在寻找身体、心灵和精神的避难所:把这个这个无趣、陈旧、墨守成规的世界忘却片刻,直到你得到满足,因为它穿过沉睡者的皮肤,陷入这个感觉性的世界,所有人都在同样平等的睡眠中做梦。侯赛因说:“不再有痛苦,不再有过往,没有任何东西能将我与其他人、计划、动物和花朵区分开来。”睡眠也是一种恢复体力的方式。
 Low Life (2011)
Low Life (2011)NK:夏洛特·贝拉特(Charlotte Beradt)的《第三帝国之下的梦》(Rêver sous le IIIème Reich)一书,开篇有一句我很喜欢的话:“在德国,唯一还有私人生活的人便是沉睡者”……
怪诞的存在
FN:这些将监视和可见性与我们生活的不同方面联系在一起的不同问题,您是如何在影片中表现的?您能告诉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您是如何处理这些影像的吗?
NK:在拍摄时,我从不在术语意义上对影像加以思考。在创作时,这与任何非常具体的事情并不对应。影像总是与我们谈论它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非我们如何构建它。在创作中,我谈论镜头、光线、机位、演员、服装、实景……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花很多时间。伊丽莎白在写剧本的时候,我在管理策划下一部电影,这也需要时间。这也是具体的。写作需要时间,也需要工具。在《下层社会》中,我对僵尸和吸血鬼等所有相关事物都非常感兴趣。两年前,我们在图卢兹拍摄了一部关于这些问题的电影。起初我们叫它《下层社会》,后来叫它《僵尸》。[5] 影片时常1小时20分钟。这是一部实验作品,是为未来的长片进行的一场实验。我们只使用了固定镜头。这是一部怪诞的电影,我们用了5个晚上,完全是在夜里拍摄的。他们是有心灵感应的僵尸,通过脑电波跨越城市交流。他们是僵固的、悬浮的僵尸。他们朗诵金斯伯格、瓦尔泽、杜拉斯、布朗肖、加比利(Gabily)、朗兹曼、帕瑟瓦勒等人的文本。我们拍摄的是这些文本在小镇上流传的过程。我们对自己说,这些僵尸就是革命前的生物。它们几乎可以生长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就像蔬菜一样生长冻结时间里,生长在岩石、裂缝、表演场地的炫目灯光、表演的意识形态、速度和商务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预先塑造了《下层社会》中的年轻人。很多时候,当我们谈论僵尸时,我们会把它们的话题局限于僵尸的类型。罗梅罗、卡朋特,所有这些……食人主义(cannibalism)、血腥、美国政治。我们更倾向于三四十年代特纳的电影《与僵尸同行》(I Walked with a Zombie, 1943)、《豹人》(The Leopard Man, 1943)、《豹族》(Cat People, 1942)……或者维克多·哈普林(Victor Halperin)的《白魔鬼》(White Zombie, 1932)、托德·布朗宁的《德古拉》(Dracula, 1931)。是关于拍摄身体的,而不是怪物。这就是我们可以考虑的演员问题。卡门、侯赛因和查尔斯。我意识到,尤其是在拍摄过程中,一切都蕴含着怪诞的东西,一切都散发着光芒,但我们无法立即察觉到。卡蜜尔(卡门)第一次出现在电影中,就给人一种奇怪的印象,仿佛她早已出现在银幕上了,好像她是从默片,从穆瑙的《日出》(Sunrise 1927)、鲍沙其的电影或特纳的《豹族》中逃逸出来的。尽管她是一位 20 岁的年轻女性,且绝对属于她自己的时代——她说话的方式、她出场和消失的能力、她既平凡又如流星般的美丽——能够完全摆脱心理学、自然主义与正式的姿势。这就是她,这些在她的天性中。Arash Naimain(侯赛因)是完全实存的,就像一堵墙,坚实、友好又不透光——我们看到他令人担忧。他有些像吸血鬼,有些像诺斯费拉图。卡门被他的存在所迷惑,就像女人在德古拉面前一样……吕克(查尔斯)在影片中是一位极其出众的美男子,带着干巴巴的浪漫主义、有点愤世嫉俗和绝望。正如伊丽莎白所说,他是爱的斗士。这可能会显得非常女性化,并激起被男性气质禁锢的男人一些奇怪的吸引力反应。它既是厄斯塔什式也是布列松式的。吕克是狼,有时甚至是狼人。
 Low Life (2011)
Low Life (2011)FN:睡眠、被麻醉状态、怪诞时刻,这些都是警察和政治僵固意志(inflexible will)的作用吗?怪象的功能是否远非一种叙事或陈词滥调,而是在与警察程序的斗争中引入的一个美学问题?
NK:当然是的。最早的生命政治电影是弗里茨·朗(德国时期)和雅克·特纳的作品。《大都会》、《M就是凶手》(M- Eine Stadt sucht einen Morder, 1931)、《恶魔之夜》(Night of the Demon, 1957)……这甚至被认为是黑色电影的开端。以及希区柯克的《伸冤记》(The Wrong Man, 1956)。这种被麻醉的睡眠状态,也是一种观众的睡眠状态。我们可以从沃霍尔的作品中看到这一点。只要一个镜头的持续时间超过预期,就会发生一些其他的事情,观众的目光会变得更加专注,我们开始看到一些妨碍着我们去理解眼前现实的东西。我们会问自己它们是否真的存在,我们问自己是否看到了它们。“你看到了吗?”《豹族》中的女公交车司机问道。与异常事物的联系,与聆听到的事物的联系,改变了它们。在《下层社会》中,我想加快这一进程以摆脱持续时间的催眠伎俩,更加精确,并让这种精确产生其他令人不安的效果。虽然仍有一些相当长的镜头,但我更感兴趣的是镜头之间的联系而非它们的长度。
 Cat People (1942)
Cat People (1942)EP:我们希望制造骚动,试图打破这该死的魔咒。在影片中,怪诞是一种传召命运的方式,同时又能避免被该类型的“石头”绊倒。例如,移民们收到的文件、他们的驱逐通知(离开法国领土的义务),非洲人称这份文件为“死亡通知”。我们从字面上理解了这种表达。这些文件带来死亡,持有这些文件的人处于危险之中,而这些文件受控于警察,或者是把文件塞进口袋的女人。当警察跟踪非裔青年时,他为了逃脱被抓捕的命运,将证件扔进了索恩河。他们都溺亡其中了;警察和非裔成了被诅咒纸张的两个受害者。动物们也感受到了诅咒存在的效用,它们变得残忍,对携带诅咒的人狂吠并且撕咬。扮演查尔斯的演员吕克身上也有一种动物性的气质,他的肢体、动作和眼神都充满怪诞。他的存在给予查尔斯一种警惕的动物性感觉,意识到那里的危险,并时刻关注着它。查尔斯是一种变种人,他能够穿过网绳,让自己隐形。追随着逃亡的卡门的足迹,追随着警察部门中的脚步……感觉我们就是这个自然的一部分,我们知道这片土地的蹂躏将所有人连根拔起。在睡梦中,主角的梦呓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失落和被遗忘的世界:森林里有大量的浆果,但无人能够采摘……以前,我们甚至看不到周遭的世界。“它就像天空,像空气。就像有人永远地把它给了我们,仿佛它将恒久存在…… 如今,孩子们在自己的房子里成长,没有森林,没有河流……他们只能在远处,在想象中看到它们。他们是另一种孩子。”《下层社会》中的年轻人出生在灾难之中,他们必须为此做些什么。就像胡里奥卧室墙上画的野牛的眼睛一样,它注视着这个世界,恢复我们的视力,最终看清那些让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之真相视而不见的虚假承诺。
 Low Life (2011)
Low Life (2011)NK:进一步解释您提出关于导演的问题,我的核心在于拍摄我在演员身上看到的东西。他们的内心世界如何与影片相结合,要跟上这点以及伊丽莎白为他们所写的东西。这正是伊丽莎白的写作令人着迷和畏惧的地方。她有一种围绕人物话语实质来构建人物形象的方法,然后我们会找到他们所要说的话。由于他们的话语往往介于致辞和忏悔之间,我们必须像在剧院中一样进行操作。这并不是因为她将其戏剧化,而是为了探索肢体、进行实验、揭发虚假的路径、演员的效果与心理学效应。我们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不分昼夜,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正是我们在这些瞬间所看到的,在这些生活中的瞬间,让我们与伊丽莎白的角色产生了联系。这是一种奇怪的、无可预见的炼金术,将我们的感觉或思维方式、我们的孤独和我们的恐惧融合在一起……就像跨越遥远距离的爱。
 Low Life (2011)
Low Life (2011)EP:关于这部电影,人们经常和我们谈论“角色”。我对此有一种双重的感觉,同时电影中人物的历史是真实的,也是虚假的。可以说,揭开演员的面纱、他们的存在,是纪实的一面,而虚构则是通过一句接一句的话语。纪实的一面与虚构的一面混杂在一起,而虚构除了在纪实中得到效验之外别无他趣。电影是现实与虚构之间的一种奇特关系。一旦这一点被您意识到,一切就都水到渠成了。在《下层社会》中,除了我认识的乔治和米格尔——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都是音乐人。我关注的是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们的梦想、欲望、愤怒、恐惧、忧虑、执着……以及他是做什么的,他是学生、失业者、工作者,或是皆不是?我对自己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怎么做?我想如何看待?我希望电影如何刻画这些青年?这些角色是一种代言人,代表着我的际遇,也代表我的孩子以及他们的朋友的。写作是这一切的结果,是观察的结果,是我们对周遭世界付诸关照的结果。我有时把《下层社会》中的人物想象成幸存者,想象成资本主义洪流下的弃儿,他们能够重塑一切,包括情感、姿态、梦想和言语。他们是寻找故土的流浪者。
 Low Life (2011)
Low Life (2011)选角期间,我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个与我笔下人物一模一样的演员,这显然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安而又富有魔力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会彼此认可、达成共识,毫无疑问,我们在奇怪的领域下相遇了。在《被排斥的人》中我们与 Momo 也是如此,甚至有人问演员我是否对他的生平做过研究。对于吕克-查尔斯,想象与现实完全相连。在几个月的准备过程中,我已经分不清吕克和查尔斯了,这对吕克和我而言都是一种强烈兴奋的体验。随后我们开始拍摄,想象再次出现,但这不仅仅是对于角色,因为吕克和查尔斯依然密不可分。
运动与省略
MG:一看到这部电影,我被一种感觉所震撼,那就是身体与欲望之间的亲和感。我们面对的显然是一个属于悲剧的存在,我们也清楚地感受到了这种运动、位移(déplacement),以及在画面中为事件出现留下的一种可能性。这样,我想到了《僵尸》、《Poptones》以及与您的作品中与《下层社会》相伴而生的电影,我记得这些电影基本上都是用固定镜头拍摄的,而《下层社会》则是用移动和位移镜头。仿佛这种身体、时间和语言的成熟是开始这一过程、以及将这一过程进行到底的必要条件。
EP:是的,运动是为了摆脱诅咒的控制,摆脱监视,重获冲动。运动是为了不被发现,就像过去的抵抗运动网络(réseau de mouvements de résistance)一样。从写剧本开始,我就看到人物在运动,思想的运动、情感的运动、身体的运动,所有这些都紧密联动。在影片的开头,一群人正在运动,他们聚集在一处违章建筑群;聚集在一起,他们遭到警察的共同反对。同时,他们也在移动,以寻找自己的爱人、朋友或对手……他们移动,他们行走,因为不再有一个固定的参照点可以供其战斗。这是一种既非顺服也非冲突,而是在一条游移的切线上生活的方式。作为旅伴,我们在人物的行动、内心活动和思想中发现自己的存在。他们为我们开辟道路,而我们则允许发现其他道路。在运动中,我们还能感受到一种顾虑,一种面对阻碍他们发展的未来而感到的顾虑。在《创伤》中,方向是由固定镜头构建而成的,它是一个方盒,向那些不再知道何去何从的人开放。流亡者不再有休憩之处,不再有地方包扎伤口,也不再有地方独处,亦或等待……
 La Blessure (2005)
La Blessure (2005)NK:我还想说的是,我非常喜欢那些我想要作为他而生存的角色,我想夜以继日地追随他们——就像热恋中的人一样!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进行数字拍摄。在对色彩以及镜头衔接的思考方式上,导演始终有偏差。我们拍摄的每部电影都是在剧本和导演的基础上构建的。例如,《被排斥的人》是一部固定摄影机电影,摄影机是固定的,可移动也可以静止;我们在拍摄时没有静止不动。在《创伤》中,我们使用固定镜头,人物进入、停留或离开画面。《人性问题》使用的是直反两种镜头。《下层社会》则采用了运动和省略的方式。
 Low Life (2011)
Low Life (2011)EP:而省略恰恰就是躲过了我们的视线。
NK:你必须与他们共生,才能理解并跟随他们的运动,如果你不和它们在一起,你就会躲避其运动。
EP:我们剪掉了很多影片中已经拍摄好的场景。我相信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故事的片段来自拍摄本身。如果要保留这些片段,我们就必须要有太多可供预测的逻辑。这样一来,故事就会占据主导地位,将比所表达的情感更为重要。就是这样,一个精心设计的故事,是控制人物的一种方式,是让他们成为傀儡的一种方式;这样我们将不再站在生活的一侧,不再站在情感或现实的一侧,我们进入了诡计之中。省略则使画外区域得以扩展,允许了更大的空间,从而造就了故事的加速和电影的整体运动。剪切是一种给观众留下更大自由度的方式,为他们留下自由想象的空间。我相信有三部电影都会有类同的场景,而这是我投注最多的一部电影。影片中的人物与我的孩子和他们的朋友们年龄相仿,我从内到外了解他们,关注他们的旅程、伤痛、征服和失去的希望。我看到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世界是如何变得黯淡无光,也看到了年轻人是如何找到应对当下黑暗的能力。世界正处于瞬息万变中,而年轻人也以其速度生活着。我们不应阻碍他们的流动性,但当思绪万千、当他们彼此质疑、当产生其他运动、当社群看到另一个世界可能存在的希望时,我们感受到的也不应当是他们的不动声色。
颤动青春
FN:从《僵尸》到《下层社会》的过渡中,有一种动作的设定,这对于一部讲述复活(résurrection)的电影来说是有意义的,已诞生的爱之复活是对一切阻碍的蔑视。我想回到“生活”这个问题,回到“生活”与“青春”之间的联系。我们今天谈了很多关于青年作为一种革命性存在的问题,在希腊,近期在英国以及在法国,在围绕着退休运动的中心,青年变得非常活跃,反抗当局的行动来势汹汹。我想请您谈谈青春的问题。
NK:影片的核心理念是,青春不是新事物,而是非常古老的事物。这就是为什么它拥有如此大的力量。青年的成长不会止步在前辈青春的废墟上。当今的青年有一种古老的力量,它只会让当局者感到恐惧,无论是来自国家还是家庭。我相信,这部电影的核心就是用镜头捕捉这股力量。也许我们之前的三部电影让我们这次拍摄了我们自己的废墟,我们这一代人一切信仰的废墟,并对电影的废墟做出理解……以及那些在废墟中苟活下来的人的力量。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青春依然是电影存在的理由,而电影的一切魅力都在于捕捉其青春;一个永不溃败的年轻人——因为她将永远拥有历史的力量。
EP:这也是有关资本主义的问题,资本主义的承诺已经变成了一场灾难。这个社会不断同我们谈论利润,谈论消费,而抛弃了青春。这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体系,它想让青年成为顺民,从四面八方对他们进行剥削,剥削至死。每一百个年轻人中就有二十五个失业;我们还看到,富裕国家的情况并不比贫困国家好多少。在这种瘫痪、这种停滞中,青年们拒绝欣然接受;他们因生命的炽热本能在颤动……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我试着表现出来,让人们感受到这种颤动。在突尼斯的街头响起了第一声警告,当时我们的外交部长提议向独裁者提供法国警察的专门技能,以帮助铲除犯罪团伙。而后在埃及、阿富汗、叙利亚、利比亚……现在在西班牙和希腊……这是为了打破秩序的魔咒,打破这种令人震颤的无能僵局。对他们来说,没有发言人,没有利益,没有政党,只需要找到必要的协议以迎接并承受这一事件。拍电影就像是大胆地参与这一事件——以电影的寓言方式参与其中。
 Low Life (2011)
Low Life (2011)NK:比如,法国大革命的参与者都是青年人。这也是我们下一部影片想要表现的……无眠的青春。这让我再次想起加瑞尔在《黎明前与你相遇》(La Frontière de l'aube, 2008)中的一句话:“我们是沉睡之人,而不是创造历史的人。”
EP:我会回应:我们是做梦之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成为领导者,将梦变作现实。
译注
[1] Canal+为成立于1984年的法国付费电视台,为法国电视四台所有,播出的多为加密节目。
[2] L'Avance sur Recettes于1960年成立,旨在推动创作进程以支持独立电影,通过公共援助来满足其财务平衡。
[3] Jean-Luc Godard par Jean-Luc Godard:1950-1984, Cahiers du Cinema Livres, p228 (谷歌图书查找)
[4] 推测为杜拉斯《绿眼睛》中的“做电影”一篇,我是按陆一琛的中译本查找的。帕瑟瓦勒在采访中对原文语句略有整改。
[5]《僵尸》(Zombies, 2009)由克洛茨与帕瑟瓦勒在2008年11月到12月间在图卢兹拍摄,拍摄工具仅为一部DV,十几名演员参演。这并不是一部已完成的电影,而是作为之后长片的一次草拟,一种宣言。
往期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