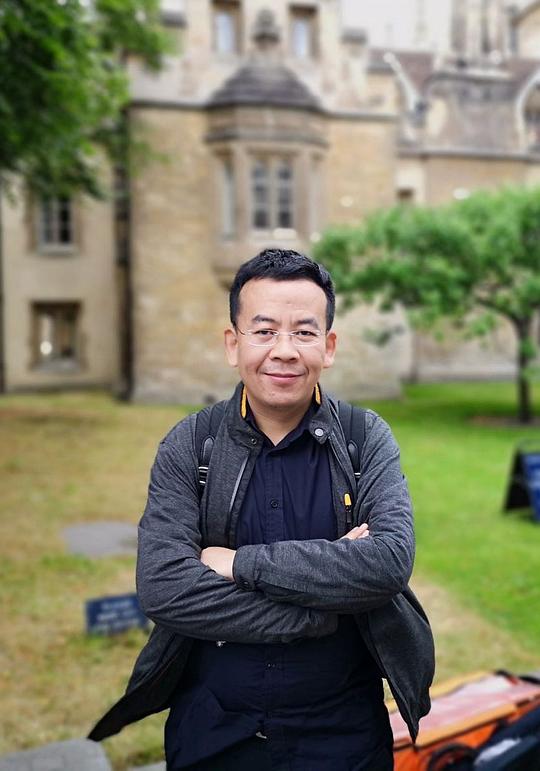美术里的中国(2022)
简介:
- 节目聚焦中国近现代经典美术作品,见证中华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的时代之变、中国之进,深入提炼作品中的文化标识、当代价值、时代意义,以最前沿的数字技术,进行融媒体视觉探索,以科技助力艺术表达,打造影像化、数字化的美术馆。通过这些传播文化、记录变迁、诉说历史的中国美术佳作,弘扬中国精神,增强文化自信。
演员:
影评:
北京跨车胡同里的齐白石,画虾须,都超慢超慢。阿芝是以湖南的木匠活计,来到北京的。和文人画传统不同,他就像是当时的白话文。吴洪亮和冯远都在极力追捧他。
说实话,我特别不喜欢。连拍一部纪录片都搞得跟艺术评论一样,没有批评只有赞扬。这就是中国,这就是美术里的中国。中国无批评。
第2集挺好用,画面呈现了五笔七墨法,这下我教学生更方便了。什么闫振强啊,于洋啊,这讲的都打不到点子上。韩劲松是书呆子气。
潘天寿的儿子潘公凯,说他爸爸找到了突破的口。翻出1953年的档案,他和黄宾虹的名字在教学名单上被划去,说明国画不受重视的程度。这和当时的中医也差不多。
整部纪录片采取了一人一画的原则,齐白石和他的虾,潘天寿和他的雁荡山,徐悲鸿当然和他的马。
《美术里的中国》
相较于《中国绘画艺术》,这部纪录片显得更符合当代年轻人的胃口。不说运用了动画技术,让静态的“名作”动起来,而且能够展现其精妙的笔法和独特的效果;而且每一集基本都没有废话,一上来就是讲作品的欣赏,谈画家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色,既通俗易懂,又深入浅出。以至于,以前在《美术》教材上看到的那些名作,自己因为“题材”,或者“外行”,不能知其微妙,不能明其高远,现在至少也清楚这十二幅名作好在哪。
另一个角度讲,这部纪录片与《中国绘画艺术》相比,因为更侧重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画作,所以与我们今天更加靠近,与《中国绘画艺术》有比较明确的先后顺序,也可以作为“续集”来看。
不过,问题还是那个问题,中国还是缺绘画大师的传记片,只能概略,无法深入。
那么,《美术里的中国》让我看到了什么?那就是绘画和文学真的很相似,就是一种表达自己的语言。在特定年代,比如国家受到他国侵略,似乎笔不如枪来得直接,无法为疗救祖国做什么。但其实坚持自己的特长,一样可以通过“艺术语言”摇旗呐喊,振奋人心,从心灵上精神上去做出自己的贡献。
至于绘画的语言有什么呢?两句话:语言是自己的,也是时代的;语言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首先,为什么说语言是自己的?如果人云亦云,那么人家听到了也不会有多大的感想和回应,所以画家都有自己的艺术特色,甚至往高点说艺术风格。不说有自己的创造,也要有一眼看到就知其精妙的“境界”。就像靳尚谊画《塔吉克新娘》,从“三角形”构图,到具体油画手法,他并没有任何创新,甚至如他自己所言“我一生都在打基础”。但是他最终是画到了一个油画艺术的境界,以至于如片中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院长杨飞云所言:“改革开放开始以后,别人往现代了走,他往那个传统是往那个根本本源上走。他是第一个啊,这个往源头上去解决问题。”所以,即便是坚持传统,把传统语言运用好,也是自己独特易见的语言。靳尚谊的语言妙处懂了,那么其他风格独特,富有开拓意义的大师们更不用说了。像傅抱石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国画的皴法,并且创造了独特的“抱石皴”(一种具个人风格的独特皴法,凝聚的笔锋全部打散,无数条细线,拽着墨痕横刷猛扫,用笔无拘无束,笔痕无起无落,勾勒出体积明暗,传递出浑厚苍茫的生命律动)。像徐悲鸿,他是主张“道在日新,艺亦须日新,新者生机也,不新则死”的,所以他“将西化的光影画法运用到画马上”,不说在当时让人耳目一新,放我们今天一眼也能判断是徐家之马。吴冠中画《太湖鹅群》“画中的用笔呢,形成了非常多的这样的机理,这种机理非常接近于我们在中国画的这个用笔里边,毛笔的那种飞白的那种印记,同时呢又非常贴近鹅毛的那样的一种蓬松的感觉。这样的一种用笔,应该说是结合了欧洲的现代油画的那种用笔的特点,同时又融合了中国画的用笔的特点,这也是吴冠中先生他强调的用笔的写意性。” 所以,不管是坚持传统,还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是以西入中,还是以中入西,最终都是找到自己的语言风格,自己的艺术表达。
而且,有意思的是,每个画家独特的人生经历,甚至说当初“被迫无奈”的经历恰好更加塑造了画家的独特风格。比如黄胄的一生大约创作了4万余张速写,而这又恰好让他的《洪荒风雪》有了独特的“速写”魅力。比如1966年到1977年,罗中立在四川大巴山区度过了十余年的乡村生活,青葱岁月中,农民的朴实与坚韧在画家罗中立心中深深烙印。他决定创作一件抒写农民的绘画作品,这样的选材构思,确定了他更能够获得最大的共鸣。比如徐悲鸿,他选择画马,这与他没有钱雇模特,只能跑到马场画马有关系。又比如黄宾虹因为战乱,受邀北上,帮助鉴定整理古画,以协助战时文物转移。在纷乱的年代里,他只能埋首故纸丹青之中,于是观摩大量古画,“在先人的山水世界中,苦苦寻觅墨法的灵魂,感受着浑厚氤氲中的气象变化,摄取笔墨丘壑中的精微表达,不断临摹,思考探索。数十年积累后,黄宾虹最终在前人基础上,总结出用墨七法,浓墨表现阴面凹陷与近景,淡墨勾勒光面凸起和远景,以浓破淡,以淡破浓为破墨。反复交错,层层积叠为积墨。泼墨以墨泼洒,焦墨干笔涂抹,宿墨则是用隔日的墨入画。”
其次,为什么说是时代的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何况本来审美就容易产生疲劳,更不要说绘画本身也是一门艺术语言,是表达艺术家个人思想感情的载体。所以,不管受制于个人能力还是时代困难,能够被时代传颂而后流传后世的,始终是能够展现时代的作品。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不管是展现流离失所的百姓苦难的《流民图》(蒋兆和),还是表达对战事担忧激奋士气民心的《奔马》(徐悲鸿),都是为时代记录,为时代呐喊而被时代所既垂青的作品。所以,到了新中国,新国画要摆脱古代士大夫“孤芳自赏”“清冷孤傲”的艺术,而是与毛主席契合时代的语言一样,展现“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磅礴气势,“山,刺破青天锷未残”的浪漫想象,所以,潘天寿《记写雁荡山花》“艳而不俗的颜色一改清冷孤傲,巨石花草画出天地之心,更画出豪迈气象”。不仅作品让人耳目一新,而且让国画契合时代精神。同样的道理,孙滋溪的《天安门前》和刘开渠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胜利渡长江》都是抒写时代,而成为经典。正如罗中立所说的:“艺术只有植根民族,展现时代精神,才具有生命力。”
再次,为什么说语言是民族的呢?中国的画家,生于兹,长于兹,自然离不开自己的语言。正如,黄胄所说:“生活是创作的根,美的源泉,根深才能叶茂。”齐白石,之所以从一位乡村的花匠,成为一代大师,成为人民画家。就是因为,他质朴地坚持着农民的根本,深刻地印记着对童年的记忆,对家乡的怀念,对生活的热爱。所以,“灵动的虾,是齐白石生机勃勃的笔墨世界中的一员,他还爱画大白菜,水灵灵的十分肥美;他画柿子、石榴、各类蔬果以及昆虫,甚至极少入画的竹耙、箩筐、算盘。”这也使得齐白石的画大俗大雅,意趣与众不同,境界反而超脱。同样的道理,罗中立画《父亲》,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只是他寻找到“超写实”的手法,选择“巨幅”去实现他的构思,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在寻觅的,去“创作一个很有分量的,这样一个能够表达中国这样一个主体的,这样一个农民群体的,这样体现一个国家脊梁他们的命运。他们实际上就代表了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命运,他们的前途的好坏”。
最后,为什么说语言是世界的呢?正如吴冠中所言,“我想造一座桥,是东方和西方,人民和专家,具象和抽象之间的桥。”艺术的语言始终是共通的。而且语言的交流与融合,恰好是艺术不断得以创新发展的关键。正如前面谈到的,徐悲鸿是以西洋法画中国画,吴冠中以中国画法画油画,更不要说罗中立以西方当时刚刚出现的“超写实”手法,创作展现中国主体的艺术形象。
2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