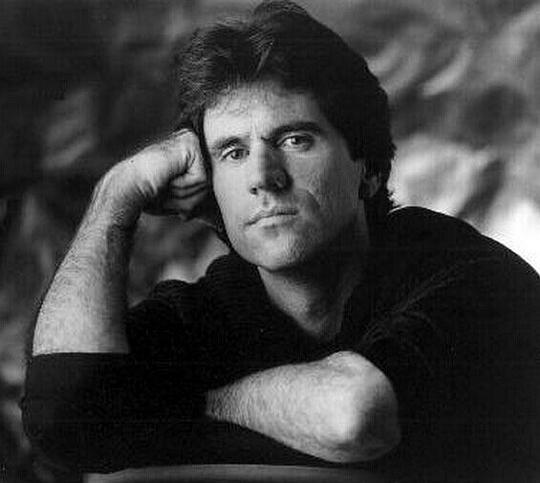艺伎回忆录 Memoirs of a Geisha(2005)
简介:
- 根据美国作家阿瑟-高顿的同名小说改编。故事以第一人称展开,时代背景从1929年开始延续到二战结束,女主人公回忆了自己从小拼命挣扎、历尽荣辱的人生经历。
演员:
影评:
坦率地讲,日本始终拥有这个世界上最为做作的文化。 那是一种紧张的假正经的文化。 近乎荒诞,乃至诡谲。 例如,我不认为恩客与艺伎在做爱之前互相郑重叩拜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简直令人毛骨悚然,这种毫无道理的仪式感。 所以事实上这是一个生活在整体妄想中的种族。 艺伎是这个妄想的组成部分。 从女子中抽离。以虚幻的形式存在。 以过度的白面朱唇,带来幻觉,成为幻觉,并最终死于幻觉。 当她穿纤尘不染白袜,踩非同凡响木屐,束上十二重清雅和服,将头发挽作堂皇扇髻,就已经不是本身肉体所能够标识的那个女人。 她成为符号。 她在指代一种身份一个角色。她把自己埋葬在衣裳、脂粉、定则和分寸的下面。 所以,即使她被爱上,也是不幸的。因为她不知道被爱的是谁。 所以,即使她爱上别人,也是不幸的。因为她不知道是哪一个自己在爱着。 她必须悲伤。 那是与吃饭睡觉,与死一样必然的事。 她必须悲伤。 更值得悲伤的是,甚至她不知道是哪一个自己在悲伤,并,哪一个自己值得悲伤。 影片中,那一夜,小百合以一支疯魔雪舞赢得万众瞩目。 半道清寂雪光映上她面孔。 如妖。如魅。如一只亮烈的鬼。 顷刻走火入魔。 在爱的境地里,实在是谁也不要立地成佛。 次日,小百合名动京城。 成为所有幻觉中最值得企及的一个。 呵,好繁艳,好华美。 然而,我更乐意看到作为女子的艺伎,盛名之后的寂寞。 最爱那场戏,初桃如同阿修罗带来哀艳的战火。 之后,她穿泼墨似黑白和服走上灰蒙蒙迂回街巷。眼神依旧强大倔强。她两手空空地消失在雾气回荡的街角。 优雅、莫测而急促。 这才是我喜欢的故事。 一个女子,爱过,希望过,拥有过,后来都失去了。 连同那个嚣艳的不可一世的身份。 应是同时有过艳与寂,在生命里。 就像光,就像风。 2006-1-5
 我的公众号:逍遥兽
我的公众号:逍遥兽- 准确的说,《艺妓回忆录》不是一部可以让人流泪或者开怀的作品,它的味道是内敛的。
从看到Sayori那双湖蓝色的双眼开始,整个故事已经有了一种澄澈但是宁静深邃的意味,东方的文化是崇敬命运的,所以这双美丽的“eyes like rain"也在冥冥中注定了这个小姑娘不平凡的人生道路。雨总是绵绵而温婉的,飘落在东方国度古老却缤纷的色彩世界中的雨丝,更是催化出了水最缠绵切切的一面。在春雨中,憧憬着生命的萌动;在夏雨里,淋漓着感情的盛开;在秋雨时,伤感着离人的悲欢;在冬雨下,期盼着新的憧憬。所以雨也变得有了灵气,所以命运如水的Sayori有着征服四季的温润魅力,一种代表了东方神韵的魅力。
是的,我是说东方的神韵,而不是那个我不愿提及的国度局限性的美丽。不得不称赞导演和他的王牌制作人索德博格的惊人的发掘东方美丽的眼里,如果没有三位最杰出的华人女演员的加盟,我一定会将这部影片打入垃圾片的行列,但是有了这三位女星的辉映,我们看到的艺妓,我们看到的从这些柔弱身段后投影出来的袅袅余香中,有着一种远远超越了那个岛国的歌舞伎文化所能传承的博大精深的对于美的追逐,有着一种对于人性的美丽的极致浓缩。不客气的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华人女演员可以在厚厚的粉脂覆盖下,在不允许面部表情流露的情况下,仅仅用她们的双眸就表达出了如此丰富的喜悦和悲伤,如此厚重的追随和渴求,如此坚毅的爱恋和勇气;同样的,这个世界上,只有源自华夏的文明,才有着如此沉稠的文化底蕴感,赋予本来如同清水般无味的故事,回味无穷的醇厚茶香。
仍然历历在目,子怡在那场轰动全城的舞秀上,飘逸的青丝,霰霰的飞雪,殷殷的朱唇,曼妙但是稳重的步履还有婆娑袅娜的身姿。从含泪的独步到绝望的抗争,这段舞蹈可以称得上是整部电影最集中的两点,那是一种”我们没有选择,所以才成为艺妓“的自卑和这种自卑中,深切的抗争渴望和追逐自由的梦。如果子怡在影片中能有三次以上如次出众的表演,我想今年的奥斯卡影后之争不会有任何悬念。
至于巩俐的表演,我是没有评论的资格的,如果我是评审委员会,一定会乖乖拱手奉上那尊“最佳女配角”的小金人。深刻入骨的看似放浪之后,是一个为自己的不自由,为自己的卑微而拼命守护最后一丝虚荣的心,当宠幸老去,铅华尽洗的时候,入髓的叛逆如火燃烧,虽然惨烈,却也焕回了另一种人性的释放和刹那光华。
艺妓表演的艺术,是浓缩了的一个个梦,而每个生命背后的那些最绚烂的梦,就如同是镜湖青阁之间盈动的翩翩落叶,每一片都舞着独一无二的舞步,每一片都在找到归宿的那一刹归于平静。
胭若茶韵人若梦,看了好莱坞营造出的纯粹而且是精华了的东方美,再看看整个亚洲地区乌烟瘴气的电影作品们,心中的冻雨在冰冷的纷飞。 - 刚刚看完《艺伎回忆录》,短暂说下感受。
故事不好。自从小百合长大以后故事基本以平铺直叙的方式进行,不论是成为艺妓,是战争,是落难,还是重逢,故事都没有任何突出的重点,各个部分笔墨同样多,真是好实在的回忆录,喝白开水喝到人撑!
爱情故事情节做作。小百合与主席的爱情完全是主观臆测。小百合的单恋还算合理,可主席对她的感情纯粹是莫名其妙:爱她,所以送她学习艺妓;爱她,甘愿让自己的好友拥有她;爱她,因为“原则”不去争取她的初夜。我是在电影里没看出来主席对小百合的爱,看到的仅仅是喜爱而已。所以影片结尾的重逢就十分突兀,仿佛为了大团员给观众一个交代硬加上去一样。小百合的幸福纯粹来自于巧合,来自于主席朋友的主动退出。这个欢喜结尾是整个故事的最大败笔。如果说小百合希望破灭那一段给影片增加了许多深刻的思想意义的话,那么这个结尾就把这些意义完全抹杀了。
章子仪几乎没有演技,表演太幼稚。越来越发现章子仪只有三种感情表现得好:单纯的快乐幸福与仇恨和不可一世。她实在是一个单一化的演员,可能生活的阅历无法让她表现五味陈杂的复杂情感,不象赵薇,经历了生活中如此多的不幸而有了《情人结》中的突破。作为艺妓,虽然小百合需要压抑自己的情感,要成为不露声色的淑女,可作为一个丰满的人物,观众是需要看到不动声色下面隐藏着的激情,憧憬,痛苦与迷茫的。而章子仪表现出来的小百合却是一个感觉迟钝的女人,除了自己心中那一点小秘密之外,外界事物仿佛很难打动她,她对任何事物表现出来的感情都是漠然,机械。在这层漠然外表下观众看不到任何内心世界,或者说这个缺乏情感的小百合的内心世界是一片空白。而同样也是把对幸福的向往埋藏在心底而表面不动生色的杨紫琼之角色,就在与小百合对话的细节里把内心的挣扎与失望通过眼神表现出来了。章的蓝色瞳人虽然美丽,可透明纯粹到一览无余。这样的单纯,在小百合15岁刚刚成为艺妓稚气未脱的时候还是合适的,可自从她登台独舞出卖初夜以后,她的眼神里就应该多出痛苦与决心、勇气等很多东西。尤其是那段雪中独舞,表现的是一种多么深刻的绝望与苦涩,能够跳出这舞蹈精髓的小百合绝不会只是一个仍然不谙世事的孩子。
巩利是这部片子的最大亮点。她的出场绝对可以称作美艳绝伦,眼波流转,不可一世。她把一位当红艺妓求爱不得,年华逝去的恨与妒简直表现到了极至,不过小柯并不觉得表演力度太过。因为在雨夜爆发的一场中,当巩利的角色被老鸨警告艺妓是没权利去爱的时候,她在愤恨之后那种对命运的绝望又愤愤不平,却依然无可奈何的表现实在让人拍案叫绝。巩利是眼睛里面有故事的女人,浑身都是风情,眼角眉梢皆是戏。当然这个角色发挥余地很大,表演的是真性情,比压抑平淡流水账般的小百合更容易吸引人。
杨紫琼戏份不多,可那种成熟艺妓的自信、优雅与从容却被她表演的十分到位。小柯认为她是整部电影里最成功的艺妓,章子仪的小百合跟她比只能算小儿科。不够优雅,不够执著,缺乏自信。
马友友的大提琴仍然一如既往的沁人心脾,声声都是情。电影画面精美,色彩突出。至于电影是否客观真实的体现了日本文化与真正的艺妓,不是日本人的我不得而知。
进电影院之前我以为这部电影是一首关于艺妓的史诗,会让我因为了解了艺妓的精湛技艺,苦难生活,了解了她们的挣扎与尊严后更加敬重这些艰辛的艺人们。可惜,这部电影的故事编排太过注重细节,情节不同部分太过平分秋色而抹杀了主题。走出电影院,小柯自问:电影究竟要表现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我回答不出来。我确是看完了艺妓小百合的前半生,不过之后心中留下的一句话只能是:“哦,原来艺妓的生活就是如此。” 没有敬重,没有鄙视,没有任何情感。这实在与当初的期盼相差太远,真真如同鸡肋:看过失望,不看又太可惜。 - 这部电影,在制作层面从任何角度看都是精品——精品中的精品。
导演:罗伯特马歇尔
制片:斯皮尔伯格
主演:章子怡 巩俐 杨紫琼 渡边谦
配角都有如桃井薰、役所广司、曾江、周采芹这样的人物。可以说这应该是当时亚洲电影明星翘楚的汇集。
抨击剧情,其实错不在编剧。原著太烂,导致怎么编都不合理。整个故事就是一个小女孩如何为爱一步一步成为业内顶尖菁英,放之四海而通杀的剧情构建在神秘的日本艺伎背景——这个背景还是作者意淫出来的。
找到阿瑟戈登的原著看了看,他非常努力地试图用英语来构筑一个他完全不熟悉却极力想要接近的绮丽世界,但是不论那些比喻如何美好(印象深刻地有比如她们的和服后端在榻榻米上如同海浪细沫漂浮之类的),语言的障碍注定了那些幽微细密潜忍的寂艳只能存在于这个文化存在的表达系统和内容中。电影之所以薄弱,也无可厚非。
有趣的是,正是这种明明知道它纯属西方人不真实且幼稚的想象,让影片呈现出了一种奇特的美感——似是而非、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仿佛被架空了的存在。巩俐扮演的初桃如此惊艳,当年美国媒体用贝蒂戴维斯来比拟她的表演,女王的气势掩盖在各种华贵的和服和高耸的发髻底下,长眉横扫,斜飞入鬓,眼神中满是不屑和野心勃勃。相比之下,章子怡的小心翼翼和不甘人下更像是外界传闻的关于她自己的成长历程,带了灰蓝色美瞳的眼睛,在某些镜头中真的会像书里写的出现“烟雨朦胧”的美感。而杨紫琼不温不火倒是没有什么突出的,但是她的姿态端庄举止内敛倒是真让人有探幽之趣。渡边谦连英俊都算不上,但是他在河上和尚是小女孩的女主角相遇在桥上的那场戏,真是迷人极了——为了这样的人终其一生而只愿意换来他的目光,才有说服力。
作为一个狂热电影原声爱好者,《艺伎回忆录》的电影原声绝对是我最喜欢的原声前十。约翰威廉姆斯作为斯皮尔伯格的御用配音不可能不出现——作为当今最了不起的音乐家,他的配乐和电影保持了高度一致——同样是自己意淫的充满异域风情的音乐,同样诠释出了不可定义的奇异美感。在电影里他没有俗套地用一般的东方乐器比如洞箫、笛子、琵琶、三味线等等,而是运用了大提琴和小提琴为主声。
好了,重点来了,大提琴是马友友!!!!!!!!如果这个还不够让人尖叫,那么小提琴的演奏者是伊扎克帕尔曼!!!!!!!!!现在,让我纵情尖叫吧!!!!!这真是三十年来史上最华丽的配乐阵容!!!!
就拿渡边谦和小时候的千代在桥上相遇那场戏而言——这个我看了不下二十遍,一半是为渡边谦低沉温柔的声音和小女孩浅灰蓝眼眸低垂的羞涩,一半就是为了在其将近尾声小女孩仿佛看到人生希望时幽幽浮起的音乐——之后镜头一转,她奔跑在通往神庙的长廊上,灰蓝色的小和服和重重叠叠的橙红色的门廊呈现了如同波浪起伏的玄幻感,马友友的大提琴仿佛从心底浮起,每一次都美得让我鸡皮疙瘩乱起,而伊扎克帕尔曼的小提琴不知何时逐渐跟随,就像是情人的声音在耳边低声絮语那种呼吸若即若离的隐秘骚动和欢愉。
后面的剧情就很烂俗了,可以说到小千代成年之后基本上就剧情直转急下,二战日本战败,艺伎没落,千代战后因为其在艺伎界的崇高地位而成为恩人与美军沟通的重要桥梁——这可以看做是对未知文明美感的向往么?
当然如果要纠结演员的英文发音那真是很纠结的事情,渡边谦、杨紫琼、曾江、周采芹的英语好得可以跟上她们的演技,而巩俐则是可以用演技来让人忽略她的发音(她的发音其实很不错),至于当时的章子怡,我只能说我看得出来她很努力……《艺伎回忆录》其时所产生的争议现在不过是鸡毛蒜皮,这个好莱坞让中国女演员来出演日本国粹之一怎么说都不算是我们吃亏吧,倒是当时日本演艺界还在懊恼为什么他们国内没有能够出演好莱坞A级制作的女演员。
这部电影让章子怡第一次获得金球奖最佳女主角提名——未必是她演得多么好,而是这种制作的电影必然会被评奖考虑,伴随而来的是演员也会获得相应的重视。这就是为什么名导名制作名演员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前几天想念原声又把电影下下来看看,果然还是会被那惊心动魄暗流涌动的音乐而激起各种思绪——配乐能做到这个份上,我也无话可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