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戏(2017)
简介:
- 1982年,隆冬时节,苍茫大地,人们在渴望春天的到来(包产到户)。
演员:
影评:
- 这是一篇,是影评又不是真正影评的文章,是影评,因为跟《村戏》息息相关。为什么又说它不是真正的影评,作为电影《村戏》的场记,我是看着它“出生”的,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荧幕上的它,而我,更想讲一些,背后的故事。
6月16《村戏》在上海博物馆首映,我几乎通知了身边的所有朋友去看,身边的不少朋友看完之后,惊讶于它的长镜头,感叹它的视听语言,赞美它独特的立意……不少人把《村戏》定义为一个艺术片,这个艺术来源于民间、用民间艺术家的表现方式展现、最后通过荧幕又把艺术归还了回去。
让我给大家,讲讲《村戏》戏外的人和事,《村戏》能与大家见面,离不开这些民间的艺术家们。
(和郑大圣导演还有我两个同学的合影,左一是我,唉,这么胖也怕冷)
那是15年11月底的冬天,我来到了这里,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去过农村,听说那里是产煤地带,而且是住在村民家的火炕,我的心就凉了半截,我相信,组里的很多人来之前都会有这个想法,我怀着忐忑的心情,从上海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梁家村,路上堵了4个小时的车程。车开了一个又一个坡,终于停到了目的地。
真的,你无法想象,12月太行山脉底下的这个小山村是多么冷,我120多斤的脂肪,外加保暖内衣、保暖裤、羽绒服的,根本不抗冻!活了20多年,在这里迎来了人生中的很多个第一次、第一次住火炕、第一次生冻疮、第一次吃农家饭…也是第一次,让我对农村、对生长在农村的这些艺术家们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
“他们行么?”“都是从来没演过电影的人”“戏曲和电影总归有区别吧”这些话,相信每个人都质疑过,包括演员老师们也可能这样问过自己。到组里的第一天,梁春柱(路老鹤)、李志兵(奎疯子)、吕爱华(树满娘)老师们正在排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装扮也都是电影里的服装,梁春柱老师手里拿着电影里的烟斗道具在手上把玩跟吕老师、王老师聊着天,李志兵老师坐在门口,一直低着头看自己的台词,好像周围的世界与他无关。现在回想起那个画面,李老师与其他老师的疏离,跟李志兵老师饰演的奎疯子与人群疏离正是相呼应的,这并不是巧合,他们早在生活中就把自己当成戏里的那个角色了,或者说,戏里、戏外,只是换了个活法儿而已。
后来我才知道,演员老师他们来自同一个剧团——陆德晋剧团,应周围县、镇、乃至村的邀请,每年的春夏秋都要出去演出。
李志兵老师在剧团里一直演的是丑角,可能大家对丑角不太了解,百度百科上解释的是,丑角扮演插科打诨比较滑稽的角色,例如,龙王宫里的龟丞相。这让我想起了周杰伦有首歌《乔克叔叔》,讲的就是小丑的故事,“你笑了之后,不需要记得我,灯熄的时候,漫天的星空,最明亮的是寂寞”,演丑角的李志兵老师,在舞台上总是把快乐带给大家,实际上自己也是孤独的。电影里的奎疯子,也是剧中的“小丑”,大家嬉他、怒他、打他、骂他,他为全村带来了荣誉、却成了全村愤恨的对象,他牺牲了自己、却得不到大家的成全,他曾为了保护集体财产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却孤独的坐在窑洞里像个孩子空手拨开并不存在的花生……他被推搡、被嘲笑、被嫌弃、成为群体茶余饭后的谈论对象,他不正是生活里的小丑么!李志兵老师能演好这个角色,不是偶然,真的是必然,他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电影表演训练,身为戏曲演员的他,冥冥之中在舞台上为这个电影角色已经积淀了几十年。
李志兵老师平时在片场,都是“慢半拍”的,有时候,你叫他的真实名字,他都不知道你在叫他,他完全进入了“奎疯子”这个角色里,听郑导说起,李志兵老师标志性的眼睛斜看向左上方是有专门的医学依据的,这是由于精神病患者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决定的,也是为了这部戏,专门去请教精神科专家,专家给推荐的标志性动作。冬天的拍摄,李老师穿着破棉袄跑遍了整个村庄,我们记住了滑稽的奎疯子:他背着枪、走着正步、幻想自己为了拯救花生的而虚拟的战斗、他接受一把根本没有的空枪,他只活在自己民兵排长的世界里走着标准的正步,他往人家身上泼粪,他喜欢抢起小女孩举高高……我们又记住了可怜的疯子:他被众人压在身下捆绑,却只记得让支书保护花生、他被人抢走了全部的花生捧着一捧花生皮向支书告状、他乖乖的坐在台阶上听从小芬的安排听戏、他被自己的儿子树满开空枪后,失落的像个迷了路的孩子…
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在吉普车内的那场戏,李老师的表演击沉了好多人,当时在监视器旁边的我,边在场记单上记边哭,我清楚的记得这场戏一共演了八遍,他哭一遍我跟着也哭一遍,平时真没那么矫情的我,实在忍不住,这比在电影屏幕上看更真实,你会觉得奎疯子是真实存在的,你是真的为他而难过,为他心痛。 连着八遍演下来,每次的情绪都有不同,每次都能给人不同的震撼,这场戏过了的时候,我还记得,李老师并没有从戏里“疯子”的角色缓过来,见到导演,李老师的眼里还有没有完全干的泪,他跟导演说,“演这个戏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能到达那种感觉,我想起来了我孩子小时候,因为一次生病,连着输了好久的液,差点没抢救过来,那种滋味太难受了……”
李老师用表演真的印证了他自己常说的那句话,表演不是为了演而演,而是为了演好,先要成为他。唉,让我怎么能够不感动,不行,再说下去,泪又要来了。(下图是和李老师的合影,原谅我笑的有点傻,哈哈)
说完主角“奎疯子”,再来讲讲“路老鹤”看过电影的人恐怕都对经常拿着烟斗、留着两撇小胡子、满肚子“坏水”的路老鹤印象很深。饰演“路老鹤”的梁春柱老师其实是陆德晋剧团的团长,同时也是饰演“疯子”李志兵老师的师兄,俩人从1985年进入陆德晋剧团到现在,已有20多年的交情。在李志兵老师接演奎疯子这一角色时,梁老师表示十分担心,怕李老师入戏太深,到时候真成了疯子。
看过电影的人,会觉得路老鹤是整个电影里的“大反派”,身为陆德晋剧团团长的梁春柱老师,演活了戏里精打细算的“路老鹤”,用最细微的动作、最精准的台词将这个人物刻画的让人又爱又恨。
我给梁春柱老师的演技起了几个名词,第一个是“眼神杀”,梁老师的眼神杀跟那些小鲜肉的眼神杀可不一样,小鲜肉的眼神里或许只有柔情,但是俺们梁老师的眼神,确是有万语!电影里,爱财的他,看到女儿小芬拉来的电动榨油机,眼里是放着光的,待小芬说道这是树满找人拉过来的,路老鹤的眼神一转,不用一句多余的台词,我们就知道他的心思了。这样的“小眼神儿“在电影里还有很多,再举一个例子,树满折断了自己的笛子,小芬拿着笛子在屋里哭的时候,在门口坐着抽烟的路老鹤,虽然只有一个侧脸,但是眼神里满满的都是戏,心疼夹杂着悔恨、坚定夹杂着犹豫、他心疼小芬、却又不忍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女儿嫁到疯子家做儿媳,也是用一个眼神便道尽了千言万语。
第二个词,是“小动作”,梁老师是个十分会搞“小动作”的人,有一场大戏,支书宣布唱戏的时候,让路老鹤分配,路老鹤在人群中间,从左边走到右边,又从右边走到左边,期间从手势到步伐换了好几个,因为机位是先从台上往台下拍的,过了几天后才拍从台下到台上的角度。也就意味着演员需要按之前的戏,动作台词都一致再演一遍。作为场记的我,生怕演员动作台词出错,因为时隔了好几天,我专门在剪辑间录了那天拍的段落,为了方便提醒演员动作。清楚的记得,梁老师的动作最为复杂,我便在准备拍的时候专门找到梁老师,让他看看视频里面,他那天的表演,以免穿帮。因为时间紧,梁老师看了一遍说可以了,匆忙赶去化妆了,其实我心里挺没底的,一遍就记住了?满心疑惑的我,在开拍打完板后,盯着老师的表演,对照着手机视频看,让我没想到的是,梁老师的动作跟台词卡的特别准,拍了几次,一次都没错……等这场戏顺利拍完,我不禁走上去,拍梁老师的马屁,不!是真心实意的夸奖,梁老师自己也笑了,说没想到自己的这种小动作这么多。但是不得不承认,多年的晋剧舞台表演经验,他们更懂得节奏,每个动作和台词无疑都在打着节拍,每个动作,每个眼神,都是戏啊!
再来说说,“支书”,饰演“支书”的王春明老师是陆德晋剧团的编导,王春明老师之前曾经可是“文武老生”,说白了就是一团正气,文武都能来!怪不得王老师演的王支书,正能量满满,看着就是一个正直为民的好官! 支书这个角色,是电影里最为中立,却最为纠结的人物。他需要站在全局去看待整个事情,想做到这点,必然要做到公正公平,这也为什么是他最为纠结的原因,因为疯子的特殊,他没有办法一碗水端平。他忘不了王奎生十年前为村里的牺牲、但是又放不下整个村子村民的利益,这个中间确实很难平衡。
王春明老师之所以能演好这样一个角色,除了他本身的晋剧表演功底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外,跟他平时平易近人的性格也是分不开的。还记得我第一天到组里的时候,王老师就专门给我拿了个烤红薯,王老师边给我边说“尝尝,村子里自己种的,可甜的很,也能暖暖手,想吃了再找我要”,王老师太能看懂人心了,他一眼识破了我就是个吃货,而且红薯不仅能暖手啊!太暖心了!从那刻起,我变成了王老师的“小迷妹”(绝对不是为了红薯!哈哈)之所以给大家举着个例子,就是想让大家体会一下,现在知道为什么王春明老师能演好王支书了吧!
支书这个角色内心的复杂,也被王春明老师表演和拿捏的十分到位,对待喜欢集中闹事的村民们,他是态度强硬的支书,几句经典的台词,在他的嘴里念出来,真让人拍腿解恨!该硬气的时候硬气——“九亩半就不是讲理的地方! ”该毒舌的时候毒舌——“九亩半我一人给你们一块,让你们闻闻自己的屎尿味! ”
对待全村人和疯子的矛盾,他又是无法牺牲大我,成全小我的支书,他为树满的事情发愁,为分地的事情忧心、为疯子的事情犯难……在奎疯子被压倒在地那场戏,支书站破落的门框下,一个背影就足以让人看了了解他内心的难过了。电影里,支书的每一声叹气、每皱一次眉头实际上都代表了观众的心声,他是每个人心里道德的标杆,又是每个人对现实无声妥协的真实缩影。正是有了王春明老师对人物精湛的刻画,才让王支书这个角色如此的深入人心!
最后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吕爱华老师了,她在电影中饰演的是疯子的媳妇“树满娘”,虽然在整部电影里,她只是个配角,但却也能让人过目不忘,吕老师在陆德晋剧团是刀马旦,专演巾帼英雄,提刀骑马、武艺高强的女性,穆桂英就是代表人物。刀马旦讲究的是人物威严稳重的气质,也是由于出身刀马旦的原因,吕老师将疯子媳妇这个角色演出了独特的魅力,不卑不亢、柔弱的身躯里透着意志的坚强、虽爱恨分明,内心却又柔软细腻。
冬天的拍摄部分,吕老师虽然只有短暂的几个镜头,却在每个眼神和动作里都十分用心。疯子回家吃饭那场戏,吕老师打掉树满的拿筷子的手,树满放下碗,几个动作一气呵成,充满着张力,动作中带着节奏,不用说一句多余的话,便已经将常年未生活在一起的一家三口的感情表现的如此清晰。支书上门说送疯子走那场戏,吕老师在叹息中透着颤音,把身体的虚弱、内心的不舍、以及对现实的无奈表演的十分到位,让观众能充分理解人物的内心。
夏天的拍摄部分,吕老师的几场哭戏真的让人跟着痛心,爱女的死,掀开棺材板撒土豆的那场戏,吕老师是真的用力咬了王奎生,被推倒后,撕心裂肺的哭,吕老师的背部都在用力,而且几遍下来,每个表演的点都控制的很好,我在现场看着,都想上去劝她别难么难过了。
一部戏下来,我真的爱上了这个地方,杀青的时候,我哭的稀里哗啦,从开始来的时候,内心充满忐忑,到现在结束了,却怎么也不愿意离开。在组里的这段生活,如今回忆起来,历历在目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一样,细细想下来,老师们确实为这部戏付出了太多太多…记得李老师为了真实的演出疯子喊口号喊到哑,真的是一遍一遍的把嗓子喊哑了…记得梁老师为了戏的需要,刮掉了他留了几十年的胡子…记得王老师的剧本早已翻的破旧不堪…记得吕老师入戏太深,导演喊停之后仍然抽泣…
(2016年夏,在陆德晋剧团演出的戏台子上,给三位试过发型的老师拍的)
艺术来源于民间,这句话,真的不是官话套话,他们就像埋在沙子里的金子,只是之前没人挖掘罢了,但是金子,终归是金子,与他们平时扎实的功底是分不开的,有人说他们幸运被导演发掘,从舞台走上了电影荧幕,导演和制片人也不止一次感叹,这何尝不是我们的幸运呢!
说实话,比起那些天价的小鲜肉,这些老师们的片酬或许都不及小鲜肉的一个零头,但他们确实是真正的好演员,不!应该说是真正的艺术家!
关于村戏!有太多话,先说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喜欢这部电影,也请大家,记住这些民间艺术家,对他们致于敬意。
最后放一张我们帅导照片!请大家支持我们的郑大圣导演,支持电影 《村戏》!看我码了这么多字的份上,小伙伴们多多点赞,多多转发!谢谢了!
2017年12月30日,大象点映联合拙见,在北京CGV星星影城,举办电影《村戏》全国首映礼,用这样一部兼具历史感和现实深度的电影跨年。
2017年12月30日,大象点映联合拙见,在北京CGV星星影城,举办电影《村戏》全国首映礼,用这样一部兼具历史感和现实深度的电影跨年,郑大圣导演,著名影视文化学者戴锦华,评论家、导演秦晓宇到场交流,同时和大象点映创始人吴飞跃一起宣布:2018年3月17日,《村戏》将在全国启动百城首映礼。下面是对谈实录。

奎生像男祥林嫂,一个即使疯了也依然活在冷战意识形态和创伤记忆里的悲剧人物
秦晓宇:大家好,我是秦晓宇,欢迎大家参加由大象点映和拙见共同主办的《村戏》首映礼,很高兴跟朋友们一起用好电影跨年。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觉得我们需要像《村戏》这样一部有历史感和现实深度的电影作品,来观照和反思那个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起点。
《村戏》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一个宣扬大公无私、却往往因公废私的年代正在结束,而个人的能动性、主体性被唤起,甚至私欲也急遽膨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一个时代正开始到来。
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一方面在经济生产上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方面在文化生活上打破禁锢,比如不再提破四旧,老戏又可以重新唱了,这些就是这部影片所表现的一个小村庄里的家国大戏。

影片的主人公王奎生,有点像个男祥林嫂,一个即使疯了也依然活在冷战意识形态和创伤记忆里的悲剧人物。他曾两次被逼疯,一次是文革中的一桩人伦惨剧,却被包装成大公无私、大义灭亲的先进事迹;一次是包产到户时期,他被路老鹤出于承包那九亩半的私心,用一句恶毒的话又给逼疯了。疯了的奎生俨然就是映照这两个时代的一面镜子。关于《村戏》有太多话题可以探讨,所以今天我们邀请了影片的导演郑大圣,还有我特别钦佩的一位学者江湖人称戴爷的戴锦华老师跟大家交流。有请两位。
我知道戴老师是50年代生人,经历了那样一个集体主义的年代,在80年代的时候也正是戴老师的芳华岁月。所以看完这部影片,您有什么自己的感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戴锦华:我其实很不习惯刚看完电影就发言,这个时候我就是个普通观众,受到电影整体的冲击,整个情绪状态还在影片的状态中。在整个电影中,我更喜欢它的现在时的层面,就是这个联产承包的时刻。很不好意思,我没看过小说原作,我想知道这个背景是原作提供的,还是大圣特别强化的排一出戏和分地?还有就是年轻人的爱情,中年人的谋划和历史,被显影为另一种色彩,我非常喜欢。其实我想先听大圣说说,他为什么要全片黑白,然后浅焦浅到这个份上?而且历史那个场景,你是用什么工艺做的?我想先听大圣说说。
郑大圣:拍成黑白是我从剧本阶段就一早想好的。因为故事的背景是在三四十年以前,这个不远不近的距离我觉得黑白影像很合适。而且黑白比较单纯纯粹,它没有那么多的颜色惑乱眼睛。对我来说有一个不远也不近、正好的距离,黑白影像从视觉上可以提供这个感觉给我。当然还有一个实际原因,我们在太行山里头拍片,北方到了冬天之后没有什么色彩,没有色调是很难看的,这是客观上的一个原因。至于红和绿是我们后期做的一个单色抽取,只留了红和绿,其他的景物和人的皮肤还保留在黑白灰上面。
红和绿的原因是我模模糊糊的视觉记忆。就是那个时间段,就那两色是色,我的视觉记忆里几乎没有其他颜色。
关于浅焦,在描述男主角疯子主观化感受的几处,我们用了蛇腹镜头,造成了光轴的随机偏移,景深平面会有即兴的模糊,不完全是能预先设计的。
悲剧性的闹剧
秦晓宇:大圣刚刚说到这部电影的影像风格,我自己在观影时有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一方面伴随着一个资本化、好莱坞化的一个发展趋势,农村故事乡村题材已经很少走上大银幕了;另一方面我们的很多影片表现乡村题材的方式又比较简单、常规。要么是一个比较现实主义的方法,用一种纪录片化的方式,比较写实的方式去处理乡村的故事;要么是带一些田园牧歌的浪漫主义表达;又或者是两者的结合。在这部电影中,我个人感觉有一种强烈的表现主义的东西,有一种黑色幽默甚至荒诞戏剧的东西,甚至用尤内斯库的一句话来说“悲剧性的闹剧”,大圣把那种戏剧和疯癫的因素融在了一个很沉重的故事里面,因而让这个故事很好看,整个看下来一点也不闷,这是我最大的一个观影感受。不知道戴老师对您刚才说到的影像风格和主题表达的手法层面上是怎么看的?《村戏》放在中国乡村电影的序列当中,它的意义和特点又是什么?
戴锦华:这是我对这部影片非常感兴趣的一点,我觉得也是处理得非常有特点的地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如何在中国银幕上再现中国乡村。至少在户籍的意义上,中国的农民有7~9亿,是绝对的多数,但是我们在大银幕上完全看不到他们的生活。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银幕,我们的摄影机还要不要朝向这个中国的多数。另外,今天在全世界范围之内,苦难无所不在,但是讲述苦难的可能性在无限缩小。就是因为人们不再接受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去呈现苦难,其实准确的说,不是不接受,是你可以这么表现,你这么表现完了以后,大家不感动。大家好像都知道,苦难在那里,然后又怎么样,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如何表现社会的问题,边缘、苦难中的人,而同时让人可以感知到他们。所以,每一次把镜头朝向中国的现实、边缘、底层或者乡村的时候,我们同时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我们用什么语言来讲述这个故事。我觉得大圣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尝试。

但是在我的感受当中,浅焦如此的突出,使我就会接收到也许不是你想传达的信息,当我们今天望向此前的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没有纵深,就是我们无法拥有一个比较长的、清晰的视野去看待它。我在看的时候有时会有焦虑,就是因为只有极近景是清晰的。一开始第一场戏我觉得效果非常好,就是光的感觉,和剥花生剥出烟尘的那种质感和那种美,表现出来特别有力量。但是到后面,有一两次的时候我就会有焦虑,我想看清楚但是我看不清楚,我就感觉它同时传递出了一种我们望向历史时的感觉。而且我也时常感觉到所谓伴随中国崛起,中国的历史纵深是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的,这个纵深变成上下五千年的,一个悠长的纵深,但是反而远的是清晰的,而近的是含糊的。我对于我心里的历史,和在座的朋友们,某种程度上也是养育了他们的父母,或养育了他们的历史,我们却不能体认,不能够进入,用科幻小说的一个词——“雾障”,就是我们做时间旅行返回过去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是白色的不可穿透的。我觉得这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有社会政治的,社会经济的,文化的,还有情感的。
所以我对电影中关于历史的段落有一点点不满足,这个可能就是亲历者和非亲历者的不同。今天在我们的印象中那个时代只有两种颜色,但是在我的感受当中,那个时代最重要的颜色可能是蓝色。所以,西方人管我们叫“蓝色的蚂蚁”,就是各种蓝色的工装形成的颜色,相反不是绿军装和红旗所形成的颜色,这两个颜色是非常短暂的时期的主要的颜色。当然这无所谓正误,我只是说一种进入和想象历史的方式。原作和你的把握当中有,可是我希望有更多的体察介入。因为这原本就是一个偶然所造成的悲剧。他拼命守住花生,这是那个时代(赋予他的使命),但是让女儿把那颗花生吐出来,最后把孩子呛死了,这件事其实是个偶然,就是在任何的历史当中都可能发生的。但是这个偶然被用作全村人得到救济粮的英雄事迹,等于全村人都出卖了他。这个故事其实是他多次被出卖的一个故事,在不同的时间段,被不同的人,为了不同的目的所出卖的一个故事。这个层面的体认和我们关于那个时代的,现在已经定性化的关于那个时代的想象之间,其实我就希望有更丰富的层次。不过,不是说那段历史被表现得有点简单,而是说,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所谓“疯子才是智者”的立论,某种意义上,疯子才是社会良知的代表,疯子就像是受难者一样,就是不断被时代牺牲的这样一种认知当中。我觉得这样有点简单,因为奎生也是一个农民,他也不是一个军人,他也不是一个受到特别感召和教育的一个角色,现在他的感觉也简单单纯了。还有就是我们尝试去触碰那些不可介入的历史时段的努力,我觉得也有点简单了。这是我小小的不如意。因为就是刚开始他出现的时候我会特别震撼,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些我期待的层次没有充分出现。

秦晓宇:刚刚戴老师说到历史的纵深,我觉得里面的古戏楼是更加有年代感的东西,远远超过了一个革命的年代。上面有破四旧的标语,“破四旧,立四新”,这么一个新时代叠加上去的东西,就传达出了这种历史沧桑感。
另外这部电影演员的选择,我个人觉得极为精彩,因为要传达的是“历史如戏,人生如戏”的一种感受。这部电影是由一个戏班子来演,就是在本地土生土长的那些人在家乡进行表演。他们是戏班子演员,同时也是那个地方的农民或老百姓,用的是一口地道的本地方言。其实我们看很多的农村题材电影,比如说《百鸟朝凤》,非常好的一部影片,但是里面黄土高原的农民都操着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这就带来了一些违和感。但是这部影片其中的人物表现的张力,特别是疯子这个人物贡献出来的,完全是一种影帝级的表演。我不知道你当时在选演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调教,还是说他们自己就如此的精彩?
郑大圣:在影片筹备伊始的时候,我只知道我不能找职业演员,因为我们的演员和明星是不可能来演农民的,尤其是三四十年以前的农民。我只知道我要找非职业演员,但是我又希望他们彼此之间是熟人,希望他们用本地的土话在他们熟悉的环境中去表演,同时他们还得能唱戏,所以这是非常苛刻的一个标准。然后我跟制片人就不停地找,最后,还真找到了一个民营剧团,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在乡间巡演的一个戏班子。于是我们就把他们整个请过来演我们这个戏。他们自己没有完全脱离农村的生活,在农忙的时候,没有演出的时候,他们还得回家,回到自己村里去干农活。当然我们开拍之前提前几周做了集中的排练,我们住在这个村里头,让这些演员穿着我们从附近几个村里头搜罗来的那个时候的老棉袄老衣服,我们的美术制景再把那个村庄做旧,这帮演员我们也想法儿做旧。就是尽可能复原当时的一个生活样态,要集中学习,要唱歌,要读文件,要念当时的人民日报,要他们背诵语录,然后晚上集中起来看样板戏,其实就是强行过集体生活,然后也模拟集会,批评与自我批评,模拟游街批斗,反正做了一些这样小型的生态复建。几周以后,我就发现他们是有变化的。当然他们自己在表演上在才艺上是很有天分的,所以我们真正拍起来的时候比较省心。
秦晓宇:我觉得这部影片不光是呈现了历史的纵深,还有对普遍人性的挖掘。比如说所有围观的村民,你也不能说所有人是无辜的。可能在这些人的合谋之下,奎生被扭送的悲剧才会发生。这让我想到了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也是所有的人促成的一个非正义事件的发生。其实这个事情也可以放在当下,我们围观网上的热点事件,那个村庄可以换成任何一个机构,任何一个空间,这样的事情也会再发生。我觉得这种事情可能是一个历史和现实交相互涉的一个故事,影片中好多的东西也能让我们想到今天。这个故事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村戏》是问题意识和创造性表达的结合
郑大圣:刚才戴老师特别说到“浅焦”和观看的焦虑,这么一说我才想到特别有意思的事。我们当时在拍的时候一个个镜头都是很现场、很当下、即兴的判断,然后我的摄影指导就问我好几次,你真的要这么拍吗,焦点留到前面,让他们自己走到那个位置上去?每次我都是很直觉地说,对对对,就是这么拍。但是此前我并不知道有什么潜在的关联。我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现在想确实是出于某种焦虑。因为三四十年以前不远也不近,但是我们不知道,在这之前就更不知道,有很多历史阶段是模糊在一起的,我们知道个大概,我们并不知道具体的细节——像是故事发展的那个阶段,红绿的那个事情,那是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影片里面意外夭折的小女孩大概就是跟我同样的年纪——好多东西是模糊的。大概知道,但是无从知道,我又很想知道,这个焦虑我是有的,这也是我拍这个片子很朴素的个人动机。但是您这么问之前,我并没有这么清晰的关联。
戴锦华:恐怕不会有太多的导演说,我拍这部电影是因为“我想知道”,通常大家会说“我知道”。所以当我们大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是带着一种我们已经“知道”的预设去看,而是带着一种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再一次想遭遇到这样很少被呈现出来的历史的期待去观影,因为这样的历史有的时候是不让呈现,有的时候是被人云亦云地呈现——我们大家如果都共同地说“不知道”,甚至很多亲历者也“不知道”,因为他被经验困住了——然后我们去试一试,我们通过这部电影去分享大圣这种要“知道”的那种愿望和他在这部电影当中“知道”些什么,同时还有那些东西他仍然非常谨慎地保持说“我还不知道”那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就会更有意思。因为‘不知道’,所以想‘知道’,这样的学术态度和创作态度是最有价值的,《村戏》这部片子是问题意识和创造性表达形式的结合。
秦晓宇:我觉得这也是大圣的一个特点,他是他这个年纪的导演中特别执迷于历史题材创作的。他以前拍摄的一些片子《王勃之死》等等,包括《天津闲人》是民国年代的,这部电影好像是你拍过的电影中最近的一个历史阶段了。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一种历史虚无感,因为在我们的宣传教育中,有一些历史是不能提的,或一笔带过的,有一些是我们未必感兴趣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活在当下。但是所有的当下都是有上下文的,不理解历史也就难以理解今天。
戴锦华:我原来不知道这些演员是戏班子,是业余演员,因为演得太好了。尤其最后那一场完整的钟馗打鬼,我觉得简直是出神入化。还有包括所有的演员的那种准确,这其实就是你作为导演的准确了,因为他们都是素人演员。
你刚才说的历史感,从空间当中传递的历史感,那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方面。其中,比如说戏台,对我来说很清晰,一出来那种很远的时间感就出来了。我还特别喜欢树满吹笛子的那场,从那个桥洞开始拉开,到上面的领袖头像出现。那个镜头,不只是一个长镜头的问题了,整个历史的时间整个在我眼前展现。所以我说喜欢这个联产承包的层面,因为把握非常准确。比如说,树满永远在吹这些样板戏,红歌,然后两个人之间那种默契和包括小芬的那种音质,我觉得都把握得非常准。然后现在他们要唱《打金枝》了,那个还都是上级领导的要求,而且还是在要宣布联产承包这样一个时刻。我也很喜欢这个层面当中对于奎生这个人物的把握,他是有可能在这样一个所谓复归的年代复归的,可是他再一次被暴力所阻止。

在我的体认当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认识,好像那个年代和这个年代是完全不同质的。那个年代是非常的异化的、变态的,现在好像是一个人性复归的。但是其实戏里面的人性的黑暗,或者说那种黑暗的集体的群众心理学的那种动力,其实又非常相像。我觉得体认出来这个东西又非常有趣。所以我刚才说小小的不满足是说,它又比较强化的是给奎生很多主观视点的呈现,所以我们没办法看到其他人的心理状态。这其实是我们今天,我老说“后见之明”,就是我们晚生,然后我们回过头看那个历史时,可能有的那种洞见。因为这不是一个特定的结构和动力,可能制造一种特殊的恶,这种恶可能就是平庸的恶,就是一般的恶。那么今天好像是我们已处在一个人可以做人的年代,其实会以另外的动力触动那种集体的恶。这是影片中已经包含了的,但是这也是我之前说的不满足,看上去已经被异化了的奎生,有什么内在的线索,而不是集体出卖他,在他伤口上撒盐这样一个行为才真正造成他的疯癫。你给了我们一部可以细读的电影,以后找机会再读了。
今天我们在寻找如何建立中国美学
秦晓宇:郑大圣导演的母亲是著名导演黄蜀芹,她的《人•鬼•情》被戴锦华老师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女性电影”,在那部电影中有“钟馗嫁妹”的情节,而在《村戏》当中有“钟馗捉鬼”,都有钟馗的元素,而且都是把戏曲和电影糅合得特别巧妙。其实当我们聊到民族电影时,我们知道戏曲和电影的渊源非常之深,然而要在电影中把戏曲运用得当也非常难,因为要使得表演成为情节有机的一部分,与叙事巧妙融合,否则很容易沦为印度歌舞片那种硬性嫁接。而在《村戏》当中,路老鹤和奎生的那场“钟馗捉鬼”,我觉得是整部电影真正的高潮,太华彩了,那种表现力,那种两个人之间的试探、配合和活灵活现的演绎,包括最后路老鹤恶毒的一句话造成的悲剧,都在那场戏中被呈现出来,钟馗捉鬼的戏,被表演者在一个非舞台空间反转成鬼捉了钟馗。我特别想听听戴老师对于这种戏曲和电影的结合有什么看法?
戴锦华:你给我的这个题目可以写很多篇论文。不过我想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时多少有了点底气,因为我们现在的电影制作不缺钱,所以我们在心理上有了余裕去想一想中国电影,想一想中国电影美学的事。包括戏曲在内的传统中国文化的这些介质,我们可以更清晰、更自觉地去看待和使用它。我觉得《人•鬼•情》当中的脸谱扮演,这种男演女、女演男的戏班文化,黄导把它用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但是我觉得我们当时的焦虑,还仍然是如何走出中国文化的雾霾,去寻找走向世界之路,今天好像不大一样了,今天我们是在寻找如何建立中国美学,建立中国的标准。现在我们拍一个很像欧洲艺术电影的影片已经不是问题了,现在年轻的导演可以非常娴熟也很有原创性地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能不能寻找一些中国美学表达,甚至夸张一点说有没有一场中国电影美学的革命,其实是可以预期的——在产业如此扩张、新人辈出的时候。戏曲本身一定是一个特别直接的资源,况且我们有这么多的地方剧种,这么多差异性的文化,所以我觉得,不必想象一个大一统的中国文化,或者中国主题,如果真的出现的话会很可怕,但是我说要有这种自觉意识,这样我们会多一点原创的资源和力量,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大圣的那一场戏是一个清唱,或者是一次排演,但是它其实已经足够了,因为属于奎生的这个疯子的扮装和表现已经足以再现钟馗这样的一个角色,而且他是一个捉妖者,所以那场戏,包括光的运用和演员的表演,我觉得都非常精彩,因为非常准确。
3月17日,大象点映将启动《村戏》百城首映礼
大象点映创始人吴飞跃:我想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如果没有非凡的勇气、才情与智慧,这样一部电影恐怕无法被创作出来,并且呈现在我们眼前。借用豆瓣上一位观众的影评,这是一部“非常难得的鲁迅式的电影”。但仅仅完成创作当然还不够,它还需要更多的放映,跟更多的观众见面,激发更多思考和讨论,这才能实现这部作品所承载的全部意义。
对于《村戏》,大圣导演最大的心愿,是为它找到一双双对的眼睛。而我们大象点映的使命就是,我们不希望只是做一个无为的看客,我们想帮助好电影遇见对的观众。应该说我们是一拍即合,但又历经半年慎重的讨论,才最终选择了彼此。
这半年来,许多人都在反复问一个问题,《村戏》什么时候能够公映?今天就是《村戏》走出影展的范围,正式进入影院与更广泛观众见面的第一站,马上,我们将在全国范围内为《村戏》筹办百城首映礼,2018年3月17日,《村戏》就将正式进入广大公众的视野,开始释放它的影响力。
来,请大圣导演一起为《村戏》拉开帷幕,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大象点映”的微信公号(微信号:elemmet),找到场次,并推荐给每一位您认为看得懂村戏、应该来看村戏的亲人和朋友。感谢!

戴锦华老师谈大象点映:吹响电影集结号
在首映礼现场,有记者问戴锦华老师如何看待大象点映这样的观影模式,戴老师回答说:
“现在电影面临的最大冲击其实是网络,网络造就了各种各样的分众,和不同的screens,把电影观众分散在各个看不到的角落当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象点映基于网络本身,吹响了集结号,开始再度召唤和集结电影的观众,把散落的电影观众重新组织起来。
另外一方面,大象点映虽然是在网络上召集观众,但并不是一个网络式的社群,因为它最终把观众都带进影院,让大家可以在影院这样一个空间真实地相遇,真实地观影和交流。电影院某种意义上是最后的社会空间之一,所以保卫电影,不光是在保卫一种艺术,也是在保卫陌生人——特别是异质性生命相遇和交流的社会空间,尤其是在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当下。
【本文由大象点映编辑,未经本人审阅,观众Parallel做了前期文字整理工作,一并致谢】
作为2017年度最佳华语片之一,《村戏》豆瓣8.2分,网友不禁表示“确实年度最佳”“今年华语最佳”“今年目前华语最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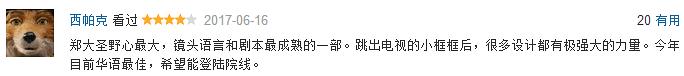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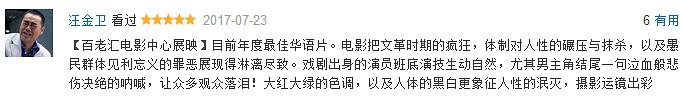

尽管电影至今没有公映,幸运的是3月17日和3月18日,《村戏》在全国数十个城市开展了点映,目前票房已经达到39万,我才有机会观看这部佳作。
希望不久之后,这部佳作能正式公映吧。
电影的背景发生在上世纪后期,有2条时间线。
一条现代线是1980年代,一条回忆线是1970年代。
1970年代,人民公社盛行,各农业社的一切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转为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
而19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国家将土地承包给农民,农民可以自我管理、生产、分配、经营,超产归自己。
农民发生了无地到有地(严格的说还不能算是“有”,因为土地仍然属于国家)的转变,人们的贪念、欲望、私心也就暴露无遗。
《村戏》的现代线发生在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将实行,人们渴望着春天的到来。
电影的第一个主题:分地。
村里即将开始分地,然而“奎疯子”王奎生却霸占“九亩半”十年之久了,不让人靠近一步。
九亩半地又好,离水渠又近,种啥打啥,因此人人都想要。
以前王奎生再怎么霸占,大家也无动于衷,毕竟大家知道土地是属于集体的;现在要分地了,村民纷纷打起了如意算盘。
明面上,大家都想得到九亩半,想把王奎生赶走;暗地里,也有许多村民偷王奎生在九亩半里种的花生。
面对村民偷花生,王奎生是零容忍,急得他满街乱转,甚至要开枪打人。
电影的第二个主题是:爱情。
自从十年前王奎生疯了,他的儿子树满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变。
树满从小就白白净净的,也被大家叫做“白小”;自从王奎生疯了以后,大家就对树满改称为“疯小”。
树满喜欢小芬,小芬也喜欢树满,然而小芬的父亲老鹤却不同意这门亲事,主要原因就是树满有个疯子父亲,次要原因是树满不会种地。
当然,如果树满没有发疯,老鹤是否会同意树满和小芬在一起,我们不得而知。
故事发生在这里,村子的形象已经有了基本雏形:
王奎生霸占九亩半十年了,导致小芬以外的所有人都不喜欢他,都想得到九亩半,还偷他种的花生。
小芬、树满两情相悦,却遭到小芬父亲老鹤的反对。
然而,真相绝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电影将回忆线和现代线交叉叙事,抽丝剥茧地还原了十年前的故事。
原来,王奎生之所以变疯,正是拜村民所赐。
原本女儿偷花生,是明明饥饿难忍,宁愿偷吃花生也不忍心动爸爸的饭菜,是一个遗憾,一个悲剧,令人惋惜,令人心痛,却被村民污名化、罪名化;
原本女儿的死,是王奎生医生挥之不去的过错,是王奎生十分后悔却又追悔莫及的意外,却被村民塑造为大义灭亲、大公无私的正面形象,摇身一变成了“保护集体财产先进分子”。
惋惜和悲剧变成了错误和犯罪,悔恨和愧疚变成了正义和荣誉。
正是这两次反差,双重打击,逼疯了王奎生。
曾经,王奎生给村民做了巨大贡献;如今,王奎生却成为了村里的罪人。
人们亲手把他塑造成英雄,又亲手把他送下神坛。
与王奎生这样的疯子相比,村民太聪明了,聪明得可怕。他们为了生存,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可以毫无人性、不择手段。
十年前,村民为了得到救济粮,强迫王奎生做不情愿的事情,强迫他说不愿意说的话,强迫他做不愿意做的英雄;
十年后,村民为了分地,又说“凭什么让王奎生白吃十年口粮”,还要把王奎生赶走。
草菅人命,弃如敝履,实在让人心寒。
老鹤无疑是最老奸巨猾的,他和王奎生曾经亲如手足,如今他却对王奎生恨之入骨,对他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成功将逐渐恢复意识的王奎生再次逼疯。
关于女儿,老鹤不喜欢树满,就私自为女儿决定终身大事,想让她和志刚在一起;
关于地,老鹤口口声声对支书说“我是村里最不想要九亩半的”,实际上也是想让志刚得到九亩半。毕竟,女婿的地,不就是他的地吗?
不管是关于女儿还是关于地,他都是为了自己。
老鹤表面上波澜不惊,内心实则是城府极深,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伤害曾经的兄弟,甚至可以做出“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实在是太狠毒。
这样一个人人为己的村子,小芬却出乎意料地出淤泥而不染,愿意站在王奎生这边。
人人都排挤、害怕、厌恶王奎生,唯有小芬一人天真无邪,始终试图去理解、包容、关爱王奎生。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十年前村民对王奎生的伤害,小芬尚且年幼,对此并不知情。
她不知道王奎生遭受了怎样的伤害,却仍然试图理解他;
与之相反,亲眼见证、决定、参与了那件事的村民,却纷纷集体失忆,对王奎生进行着二次伤害。当初他们利用了王奎生,如今利用完了就想将之抛弃,王奎生在他们眼中就像是一个工具。
换言之,一个人是否能理解他人,不是取决于Ta是否了解对方的过去,而是取决于Ta是否善良。
如果说《大佛普拉斯》告诉我们:有钱人的世界都是彩色的;
那么《村戏》就是告诉我们:现实、社会、人性都是灰色的。
人性是复杂的、矛盾的、多面的,不是黑色,也不是白色,而像电影的色调是灰色的。
在电影的海报上有这么一句话:
没有一个坏人,也没有一个无辜的人。
这句话可以说是电影的主旨。
尽管村民和老鹤如此自私自利、见利忘义,但他们并非十足的坏人。
我们观看电影的时候是处于上帝视角,可以清晰地知道每一个环节,清晰地知道谁得到了什么,谁受到了伤害。
但现实生活中,我们人人都有利己之心,但我们往往在追求利益的时候,伤害了他人却不自知。
(只不过不同的人追求利益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对他人造成伤害的程度是不同的。)
村民因为私心,伤害了王奎生;
王奎生解不开心结,最终疯了;
而小芳却说: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做小芬那样的人,面对不同的三观、行为、性格、想法,少一点伤害和排挤,多一点包容和理解。
面对这样一个充斥着自私、恶意、伤害、坏心的世界,王奎生忍痛告诉女儿:别再投胎回来了;
但是十年后他转变了观点,小芳的善良刷新了他的看法:彩云,回来,我给你洗脸。
因为与其选择逃避、狭隘、偏执、愤青,不如选择面对、包容、豁达、温柔;
因为只要像小芳拥有一颗赤子之心,就可以所向无敌、坚不可摧;
因为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
倘若站在村民、老鹤的角度考虑,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毕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但是,我仍然想像小芳那样“善良”一点。
正如《奇迹男孩》的台词:
如果在正确和善良之间必选其一,我会选择善良。
3月19日晚,导演郑大圣做客“大象点映直播间”,和大象点映(微信号:elemeet)百城首映礼的观众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在线交流,聊《村戏》的创作故事,和选择在大象点映做众筹点映的意义,并透露下阶段的创作方向。

一、谈小说改编:根据贾大山小说做延伸式的想象和改编
问:《村戏》作为小说改编电影,受到了原著的何种影响?
郑大圣:其实这个片子从筹备之前改编之初,我最朴素的初衷就是受到小说文字的感染,受到文学力量的感召。贾大山的小说写的简短、白描、朴素,没有写出来的部分比写出来的部分要深厚的多,这是一个非常深厚的留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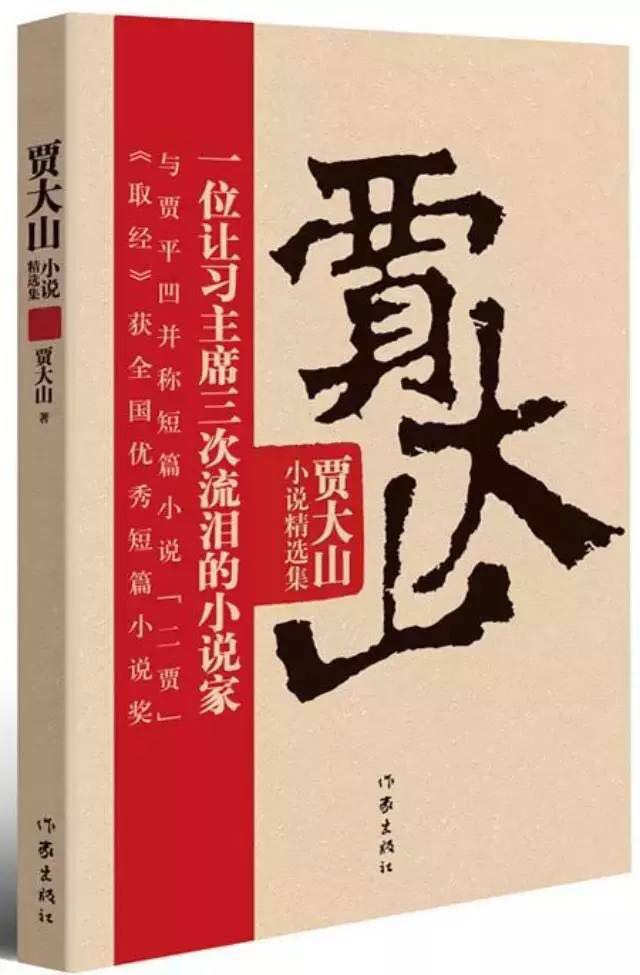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来《贾大山小说精品集》翻一翻,每一个故事都很短,看起来一点也不累,你很快就能把这个故事看完,但是隔几天以后你会想着又去看看,再翻一遍它也还是很清淡的,很平易的,貌似什么也没发生,貌似什么也没写。但是过两天你想想好像他又写了很多很多。像这种以少许胜多许的写法是很难的、很高级的。我们的改编和拍摄试图沿着他写出来的部分尽量地去延伸想象他没写出来的部分。
问:通常电影中有偏执狂、精神失常这样的角色设定的都会有很明显的指向性可以让观众一眼就看到底。起初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不设定奎疯子这样的人物呢?就是全村人都是看似正常的,这样的设定拍起来戏剧性会被减弱,不知道导演对这种主角设定有什么想法吗?
郑大圣:在12稿剧本之前,我们做过8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梗概。在这些方向完全不同、结构完全不同、用意也完全不同的故事里头,我们的男主人公存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有装疯的,有没疯的,有半疯的,但是我们觉得都不对。当我们尽可能设身处地去感受男主人公时,我们觉得他只可能变疯。发生那样的事情,身处那样的一个境地,如果他还是个人的话,他只可能变疯。如果他还能够维持一个哪怕是貌似的正常,那他也太忍心了,他真的不能算个人了。
二、谈拍摄困难:所有筹备时以为的困难都异常顺利,但...
问: 拍摄期间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郑大圣:我们分为冬天、夏天两季拍摄,所有我们筹备的时候以为的困难其实都异常的顺利。我们担心过找不到合适的场景,因为现在35年、40年过去了,太难找到还保留当时风貌的村庄,但是在井陉一个县内,我们很轻易的在相距不远的三四个村庄找到了我们所有的场景。我们曾经担心找不到那么既朴素生动,又极具表演天赋的非职业演员,但是我们在井陉也找到了。
但是在拍完冬天的32天戏份以后,也就是1980年代初的那个部分,接下来将要拍的是十天的夏天戏份,也就是1970年代初的那段闪回的部分之间,有半年多时间我跟制片人是异常的焦虑,因为我们遇到了一开始完全没想到的最困难的问题,就是那九亩花生地的问题。

照常理,花生应该是在夏收之后夏种,然后在秋天的时候结果。但是因为我们有拍摄周期的要求,不能够耗过整整一年,我们必须逆季节自己种植九亩花生。所以我们是在清明以后下的种。当时老乡都觉得匪夷所思,清明以后下种在太行山区那么冷的地方,很可能是要被冻坏、被冻死,根本长不出来的。
我们从县上农科站请了种植技术的专家来指导我们如何逆季节把这九亩花生给种出来,我们用了地膜技术,我们请了八户老庄稼把式,很资深的八个大爷帮我们照顾这九亩花生。因为花生其实特别费人力,它的这个施肥浇水都是点铸法,它一簇一簇苗得用勺一株一株的去喂,锄草也完全像战斗。
所以专家教给我们的锄草程序和手法,完全就像是兵书。所以我们在等花生的那半年间,我们的制片人非常紧张,每天都要关注河北太行山里面我们那九亩地的长势。我们请八个大爷轮流值班去料理那片庄稼,今天谁值班谁就给我们发微信图片。然后你可以想象在漫长的几个月里,那片地毫无动静。即便天气转暖了,我们那片地还是见不着动静,就是根本就长不出来的样子,我跟制片人非常担心,这个是最揪心最困难的一节。
问:据说制片人朱斌老师在拍完《村戏》之后成了花生种植专家?
郑大圣:我们制片人朱斌老师非但成了起码半个花生种植专家,事实上朱老师的心态就跟老地主是一样的,“我们的苗怎么在地底下还没露头呢”,露头了以后一开始特别高兴,跟我说“导演,花生长出来了”,紧接着又开始焦虑,“它不会只长这一点点吧?它能不能再长大一点啊”,特别像个老地主。
三、谈演员表演:他们都是了不起的民间艺术家
问:导演,我觉得您选的演员演的太好了。看过一些您的采访才知道他们都是非职业演员,我觉得演的太真实了!
郑大圣:我们所有的成人演员都来自于井陉县的一个民营戏班子,他们是唱山西梆子的,也就是晋剧。我们的男主角李志兵是这个剧团里头的丑角,他在台上主要演滑稽角色。他最受当地老乡喜闻乐见的舞台形象是《哪吒闹海》里的龟丞相,他自己研究出来的一种可以随意扭动他的脖子、步伐很逗逼的“乌龟步”。在戏里他演那样的角色,但生活中他是一个很平静的人。
我们的演员确实特别棒,拍戏的每一天他们都能带来惊喜。我跟摄影、录音、灯光每天看着监视器的时候,越看越喜欢,同时在心里暗暗称奇,他们确实特别天才,虽然名不见经传,但都是了不起的民间艺术家。
问:看完电影,我感觉奎疯子并没有疯,他只是不愿意再用世俗的态度去面对那个时代下的人,他只有用这种疯癫的状态才能将村民逼远,才能去保护他的九亩半,才能真正的遵从自己的内心,导演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郑大圣:疯子到底是什么时候变疯的呢?这就得说到我们的制片人朱斌老师,他替我们男主角在石家庄请到了一个非常资深的精神病专家来做我们的顾问。首先我们制片人是带着我们的剧本去请我们的精神病专家顾问做诊断。我们的顾问看完剧本以后诊断我们的虚构人物男主角,说你们的主人公是一个典型的间歇式精神分裂症患者。

怎么间歇,怎么分裂的呢?那就是他在糟糠和抑郁两级之间没有过渡,而且很难辨别是因为受了什么样的刺激,在一个什么拐点忽然蹦到了另外一级。我们的专家告诉我们,精神病患者心理结构的崩溃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在某一个特定的一点,一下子就转成了那个病态,而是他心里的阴影裂缝其实早就存在,裂缝逐渐加深加大,变成了一个潜在的沟壑,而表面上未必就能看得出来。所以我们不知道在某几个瞬间,因为哪几根稻草,他轰然倒塌和崩溃。
我们男主角疯子犀利的眼神其实不是臆想的,是我们制片人带着我们男主角反复走访精神病防治中心,贴身观察得来的。而且是医师提示我们的,就是精神病患者的眼神与正常人有很大的不同。
四、谈《打金枝》和《钟馗打鬼》:村民们因为利益呈现出来的众生相比戏曲更精彩
问:请问导演选《打金枝》的用意是什么?
郑大圣:《打金枝》在传统的戏里是特别典型的一个中国戏,它其实是一个最理想化的中国家庭伦理大戏。因为郭子仪是再造大唐王朝的英雄,是在安史之乱当中匡复天下的一个联军司令,所以他个人的功名是最辉煌的。民间传说他有七子八女,儿子们娶媳妇都很成功,生孙子也都很成功,闺女们嫁得也都很成功。这是最成功的一个家庭,中国人的人之常情里头认为最理想最圆满的人生,就是《打金枝》,特别有代表性。
我们的演员们和他们的路德晋剧团,他们常年在乡间演出的时候,乡民们最愿意点的,尤其是在过大年过春节期间,最受欢迎的剧目就是《打金枝》,那也是他们剧团的看家戏。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因为他们的特性,也因为在民间受欢迎如此之高的程度,选了《打金枝》。
问:为什么最后那出《打金枝》还是没有演出来呢?
郑大圣:我想,在《村戏》这个片子里头,最热闹的、最有趣的、最不堪的戏,其实是这些村民他们自己的各种情状,他们为了利益展现出来的众生相,这利益不光有田地,还有婚嫁,还有跟以前事情的各种纠结,不论是已经忘掉还是假装忘掉,大家都默契的不提及。所有这些沟沟坎坎、苟且、争夺、博弈,这本身就是一出极其热闹的戏。
他们排演的《打金枝》是给领导们看的,是为了讨好领导使得他们村庄能争取到分地的机会的戏,这就远不如他们自己更有戏剧性。所以在我们的片子里面,一直在排演的那出《打金枝》并没有正式上演在画面里,我们只是在片尾字幕升轨的时候有一段非常彷徨、非常热烈、非常激扬的一段乐曲,那个就是《打金枝》的序曲。所以我们是在升轨上让《打金枝》在片尾的时候演了一下,但是在画面里并没有演,因为他们本身比《打金枝》好看多了。

问:电影中路老鹤最后那出《钟馗打鬼》有什么特别含义么?
郑大圣:《钟馗打鬼》这出戏在北方的乡间过年的时候是特别被追捧的,乡间会请戏班子全副装扮的扮上钟馗的戏,到村庄的每一户人家,进院子、屋子跳钟馗,要走过村里最重要的道路,也要在水井前跳钟馗,这其实是一个民间祭祀的遗风。人们相信钟馗镇邪,镇压妖怪,驱除瘟疫,会给这个村庄每一个人带来吉祥,小孩茁壮成长,老人家长命百岁。这是民间很流行、传承了很多年的礼俗。
除此之外,钟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极度冤屈的形象,然后变成了一个很愤怒的鬼,而且成了鬼雄,这个戏曲传说里的人物跟我们男主角之间在命运上会有一些照应,所以我们有一个长镜头是男主角在老鹤的鼓点之下跳钟馗。
五、谈色彩蒙太奇:这是我对那个年代的视觉残留
问:请问大圣导演,颜色的选取时是怎么考虑的呢?为什么选取这几种颜色,以及是先确定了黑白,再确定红绿,还是相反的过程?以及两种颜色的切换的逻辑是什么?
郑大圣:最早从做故事大纲的时候开始,我就知道这将是一部黑白的电影,所以是先定的黑白。一直到做后期的后半场,才决定在闪回的部分要单色抽取红和绿。红和绿只是出于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在我刚开始记事的时候,正好是1970年代初,我能记得最鲜明的颜色在当时就是军装的绿和旗帜标语的红,这是我的视觉残留。同时在画面快速的闪入闪出这样的结构当中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一眼就能辨别的视觉标识,而这种单色抽取出来的红和绿就很显眼,在快速剪接里用红绿做标识很好用,所以就做了这样一个处理。
其实我们对红和绿的饱和度,并没有做过渡的渲染或者是加强甚至是变形,我们只是尽量地还原到了当时1970年代初这种红和这种绿真实的色调,我们是比对着60年代末70年代初,尤其是1968年我出生那一年,《人民画报》的封面从第一期到最后一期都是这样的颜色,我们是比对着《人民画报》做的色标。
六、谈脸上抹黑的细节:这是北方偏远村庄的小迷信
问:疯子为什么要往地里撒花生?
郑大圣:对于男主角奎疯子而言,他的女儿永远活在这个地里。他是看得见小孩的精灵的,这片地对他来说就是女儿,他得守着它。他女儿意外的死亡,其实是因为小孩儿肚子里没食,肚子里没油水,饿呀,他得喂饱她。
问:彩云盖棺时奎疯子把孩子的脸抹黑有什么说法吗?盖棺时奎疯子说彩云别回来了和抹黑脸有关系吗?
郑大圣:在北方乡间很偏僻的地方,北方的乡间会有这样的民间的风俗:小孩的夭折如果是因为不吉利的原因,比如说瘟疫,或者是不体面的原因,比如说像小贼小偷意外的夭折,家人会不希望他再投胎找回本家,这时就会用脸上抹上锅灰来阻挡他的投胎,阻挡他的轮回。北方很多偏远的地区有这样的小迷信。

问:最后奎生在车上说想让闺女回来,是纯粹的想念,还是他意识到新的时代要来了,也许有好日子了,所以想闺女投胎回来?
郑大圣:1970年代初,在女儿下葬的时候他对着棺材里女儿的小尸体说“别再投胎回来了“,等经历了十几年这么多的事情,尤其是分地的风波之后,他在进精神病院的路上说“女儿回来,爸爸给你洗脸”。这一前一后,我跟编剧讨论,跟演员揣摩,一直在体会,我们觉得都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的原因使得他这么说的,这背后有很复合的主客观的各种情境,才让他说了这么简单的两句话。
七、谈片中角色选择:当事到临头、利益切身,我们谁都不是圣贤
问:宣传语说,没有一个坏人。但路老鹤难道不算坏人嘛?尤其是最后对奎生的刺激?
郑大圣:我想这个村庄里所有的人,没人想做坏人的,谁也不会存心去害别人,更多数的情况就像我们自己,是被裹在人群里的,人群走向哪儿,我们也都走向哪儿。在这个跟着大家走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尽量地争取到自己的利益,世事大抵如此。所以我说我们这个戏里头其实并没有坏人。只不过事到临头、利益切身的时候,我们都没法要求自己变成圣贤。谁也不是圣贤。
 村长(左)和老鹤(右)
村长(左)和老鹤(右)问:导演你能不能结合当下的文化政治环境,谈一下您对村支书这个角色的看法,他的很多做法似乎很代表了民意,也处理的很不错。
郑大圣:支书这个角色很为难,恐怕是这群人里头最为难的。他不光是领导,他还是家长,他还是路老鹤和疯子的朋友。而且在乡间社会,一个封闭的熟人社会,谁跟谁都沾亲带故,我们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很可能他跟那三个小孩,从辈份上、亲缘上可能都是亲戚。所以这么些身份叠合在一起支书很难为,咱们不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我们应该能体会他是一个非常难为的人。
问:谢谢导演,90后也很喜欢《村戏》。因为现实生活中好多路老鹤一样的人,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个像小芬一样可贵的人,保持自己的善良。您对此怎么看?
郑大圣:如果我们碰到剧中人类似的情境我们会怎么办?我们可以怎么办?我们希望自己怎么办?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只能这么办?如果看完《村戏》这个片子,大家免不得情不自禁会问自己这些个问题的话,那是这个片子的幸运,也是作为导演我的幸运,这个片子就不算白拍。
《村戏》这个故事设置在1980年代初,以及回溯到更早,1970年代初,所以离现在也已经有一个不小的时间差距,但其实这个隔代也没有那么远。一些亲历过那个年代的年长一些的,比我年长十多岁的观众看完跟我说很真实,觉得有很直接的让他们刺激起回忆来。比如当我的高中语文老师跟我说,你是很真实,但是也只是揭示了那个年代小小的一角,这个是我很感触的。
我也碰到过更年轻的观众,在某一次放映后交流当中,有90后的观众说,那个年代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片子里的人和人的关系,一群人跟一个另类的个体的关系,特别像我们公司,紧接着有一个00后的观众说,发生在我祖父祖母那一代人这样匪夷所思的故事我不清楚,但是这个片子里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和我们班级一样。我听他们俩这么说,我很难以描摹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他们能够看懂,而且很耐心地看完,作为导演我当然非常高兴。但是以他们这么年轻的岁数,他们会觉得故事里的情形跟他们的工作环境,或者是班级里的处境是一样的,我也会感到悲哀。
八、谈音效设计:想要戏曲当中锣鼓点的那种节奏感
问:我对奎疯子听花生榨油联想到战争画面的那一段印象深刻,请问这一段的灵感来自何处?
郑大圣:在疯子的臆想当中,这一村人都是他的敌对方,因为他们经常到花生地私下里去偷拿花生,在疯子的认知里头,这片地当然是生产队的是公家的,怎么可以私自去拿呢?所以他们都是敌人。对于一个曾经很荣耀地当上过民兵连长的疯子而言,他的时间永远就停在了当年的那个点上,而那是70年代初的时候,是一个全民皆兵的时候,是全国人民准备核战争爆发的时候。
问:大圣,能否简单谈谈本片的音响设计?做得太棒了!
郑大圣:我们的音响设计也确实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和功夫。从前期录音到后期的编辑制作,跟影像处理在同样的一个方向。我们想把日常的生活情境处理得更有剧场感。所以我们利用了很多生活中现场实录的音效、动效,到后期的时候通过加料、重新编排、人工合成,做出我们想要的声效,主要是让它组合为一种类似于戏曲当中锣鼓点的那种节奏、节拍和配比加入到拍摄之中。

九、谈片中标语和符号:没有任何象征意味,只是视觉还原
问:导演好,很想知道电影中村子里的相关年代标语、马恩列斯毛的头像都是美工作品或购买的,还是确有历史遗留?有没有有趣的故事能与我们分享?我个人感觉这类符号在视觉上稍微有点儿多。
郑大圣:村庄墙壁窑洞里的那些标语、画像是我们的美术部门花了很大的力气,按照当时那个时代背景的真实情况,很用心地在村庄里头复原的,并没有刻意加强什么。其实这些画像、标语、板报,并不是任何有象征意味的符号,那都是基本的一个视觉的还原。以当时铺天盖地的密集度,其实跟现在商业广告的视觉轰炸、无孔不入的密集度是很相似的。有大量的历史照片做了我们还原场景的依据,我们只比当时的老照片要轻简。
十、谈版本:现在上映的版本就是最终剪辑版本,也是我自己认可的版本
问:现在我们看到的版本是最终您自己满意的剪辑版本吗?还是有所删减的?
郑大圣:现在放映的版本就是最终版本,这是我们自己认可、审查机关也认可的版本,所以我们没有其他的版本。
 保存图片,并用微信扫码,即可参与《村戏》超前点映
保存图片,并用微信扫码,即可参与《村戏》超前点映十一、谈公映:乐意通过大象点映找到“对电影有好奇心,对现实处境有问号”的观众
问:导演,请问《村戏》会在什么时候公映呢?
郑大圣:现在《村戏》是由大象点映,以召集点映的方式面向观众,我们试图找到合适这个片子的观众。因为如实的说,《村戏》这样的一个非商业类型、没有明星、甚至也没有职业演员的一个农村题材的黑白片,它并不适合于所有的观众,它对观众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特别愿意用大象点映的方式去找到对电影有要求的观众。
大象点映的这种精准推送模式对我们《村戏》是最合适的方式,它帮我们找到对的观众,找到那些对电影有好奇心和期许,对现实处境有问号的观众。感谢大家关注《村戏》!任何一部影片只因观者才有了生命。很幸运,《村戏》能找到这样的观众!
十二、谈下阶段创作计划:有意尝试迷你网剧
问:您下一部作品自己期待做什么题材?
郑大圣:我现在正在准备剧集的方案,还在创意筹划的阶段,想试试看。因为我自己一直是追美剧和英剧的,我很喜欢他们那种格式和篇幅,它能够长到足以展开电影所来不及展开的余地和容量,但是又没有长到必然把戏剧性摊得很稀薄,我想试试这样的创作。当然,我下面想尝试做的应该不是电视剧,而是迷你网剧。
问:您的迷你网剧也是打算拍一些比较沉重的题材吗?
郑大圣:一片一世界。我的下一部电影或者我现在想尝试的迷你网剧剧集,应该会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完全不一样的内容。我希望自己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