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鸟和小鸟 Uccellacci e uccellini(1966)

又名: The Hawks and the Sparrows / 鹰与麻雀
导演: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编剧: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丹提·费瑞提
主演: 托托 尼内托·达沃利 费米·贝努西 Umberto Bevilacqua Renato Capogna Alfredo Leggi Pietro Davoli 雷纳托·蒙塔尔巴诺 Rosina Moroni Flaminia Siciliano Lena Lin Solaro Gabriele Baldini Giovanni Tarallo Ricardo Redi Vittorio Vittori 罗萨纳·迪罗科 Cesare Gelli 维托里奥·拉帕利亚 Francesco Leonetti 多明戈·莫都格诺 菲德斯·斯塔尼
制片国家/地区: 意大利
上映日期: 1966-05-04(意大利)
片长: 89分钟 IMDb: tt0061132 豆瓣评分:7.9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演员:
影评:
这个时代的资讯真是丰富,媒体、书籍、杂志、报纸、网络,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但你仍然会有查不到的东西。在众多的电影书籍中,我们可以找一个电影大师的至少一部著作或是文献资料,而在这些大师的名字当中,却找不到帕索里尼的名字。最近,在崔子恩的新书《光影记忆》中也曾提到这个问题:“因着译名的缘故,中国人会在不经意间把帕索里尼和另外两个当代意大利人联系起来,一个是墨索里尼,一个是费里尼,帕索里尼在中国的荣辱,由此可见一斑。”
好在帕索里尼的电影作品还是有机会见到的。像“生命三部曲”的《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天方夜谭》。以及那部惊世骇俗的《索多玛120天》。这些涉及到情色内容的影片已经出现几种不同版本的DVD。除此之外,帕索里尼早期的一些电影的影碟也陆续推出,大约两年前,看过他的《罗马妈妈》。最近买到的是《麻雀与乌鸦(The Hawks and the Sparrows)》(大鸟与小鸟)和《定理》。
在1966年的《麻雀与乌鸦》中,帕索里尼在电影里设置了一个拟人的角色——一只会说话的乌鸦。父亲和儿子走在征收费用的路上,一只乌鸦在半路串了出来,与他们同行。一路上,乌鸦充当了一个哲学说教者的角色,谈到宗教以及马克思主义,他为父子两人讲述了僧侣传教的故事。
年老的僧侣接受了圣弗朗西斯库斯的任务,去向鸟类传教。跟随这个老僧侣的还有一个年轻的僧侣。这孤单的两个人一起上路了,他们的目的是先学会鹰和麻雀的语言,然后向它们传达爱的意义。他们花去一年的时间,老僧侣终于学会了鹰的语言,并向它们传达了关于爱的意义。年轻的僧侣只是陪同和见证,他总是在嬉戏与玩耍,没有耐心。也就是这种贪玩给老僧侣带来了“灵感”,因为他始终学不会麻雀的语言,而看到年轻僧侣在跳跃的时候,他恍然见明白麻雀之间的交流是要用跳跃来完成的。就在他们把爱的意义传达给麻雀后不久,在他们返回的路上,看到一只鹰从天而降,来地面捕杀一只麻雀。圣弗朗西斯库斯知道后,只好让他们重新踏上传教的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说教的虚弱:虽然都传达了爱的讯息,但斗争仍然存在。这不是因为被说教者不懂的爱的意义,而是有更复杂的原因,无法抵制这冲突。暗示也是明显的,人类都懂得“爱”的含义,可还是有战争,有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争吵。教士们的说教行为也许会像西西弗推动巨大石头一样徒劳,但这过程却有它自身的意义。
乌鸦的故事讲完,父亲和儿子来到一个穷人的房间,她们家的孩子已经两天没吃上饭了。可是,他们还是不放过勒索的机会。其实这父子二人也是因为还不上别人的钱,才去找比他们更贫穷的剥削。乌鸦所讲述的那个关于“说教”的故事本身就是对他们的说教。而父子根本没有拿这当回事,说教的意义在这里再一次被削弱。
而结尾处更富有意义的是,父子二人将乌鸦烧死。这不仅仅是表明对说教本身的抵制,更说明人们面对真理时的恐惧,他们不愿意身边总有一面镜子照出自身的丑恶。人们总害怕被揭示,害怕面对本质。当人与人的言谈中出现了严肃的本质,就会发现交往中微妙的变化。镜子一定要被打碎,而乌鸦正是那面被打碎的“镜子”。
有的评论说帕索里尼在这部影片中故作高深,想要给人们讲述深刻的道理。这其实是不可避免的,他的思想境界达到一定的水准,就很难体会低于他思想的状态,他不知道如何把握这种状态。像帕索里尼这样有“野心”的导演,肯定是往更高的地方走,也许当今社会不缺乏被教导的机会,加上某些美学思想不赞同这样“知识分子”味道浓厚的电影,看来就不需要这样一部教育人的电影。即使是这样,在当时那样的一个年代,能够出现这样一部艺术的关于哲学的电影文本,对人们的精神生活来说,还算是一件幸事。—
经历过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子民对《喀秋莎》不会陌生。它对我们有一种奇异的引力,如涨潮落潮般,不由自主地挑起集体主义的生理响应,导向那庄严、激荡的革命记忆。但当这熟悉的旋律在意大利荒地景观中缓缓升起,并带着一种悠悠丧钟的氛围时,无所适从的荒诞感便深深缠绕着观众的神经。 帕索里尼是狡黠的,他取消了宏大叙事下自我感动的伪装,无效化那冠冕堂皇的革命书写,并直接把其送向虚无。 电影是会传播意识形态的。卡拉托佐夫在《雁南飞》中于战争与爱情的抉择中奏响了这革命的乐章(组图1),以一个惊世骇俗的移动长镜头把家国情怀推向神话的巅峰。其实,无论是爱与战,还是家与国,真切的灵魂之痛、思绪之苦是不存在的,人们更倾向于无止境地放大“崇高”时刻,并乐此不疲地承受/享受。而电影便沦为共享以致宣扬这种伪抉择的工具。

在框架之内思索是不可能存在危机的。 《大鸟与小鸟》首先拒绝的就是虚伪。影片开场一轮明月在乌云中若隐若现,伴随着悠扬的意大利唱腔,为我们把人物娓娓道来。晴朗的月夜是适合讲述故事的。“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为你诉说,其感情保持纯真,但也略带狡猾......”,这是标准的史诗话语,是作者对表意真实的强调(史诗的真实往往不在于故事本身,而在于表达的意义,就如《荷马史诗》那样)。托托父子以中间阶层的切片被置入影片,上有大资本家的压迫,下有更贫苦的人民以供剥削。而会说话的乌鸦,作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隐喻,伴随着父子无目的地的行程。 一矮一高,一老一少,这样的主人公父子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堂吉柯德与桑丘潘沙这样的骑士传说(组图2),因而与遥远的文学传统产生呼应(影片本身也具有很强的文学性)。父子关系融洽,我们丝毫不会怀疑儿子未来对父亲的继承。帕索里尼或许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暗示这一小资产阶级的复杂性,可悲中参杂着可恨,却又没有十足的罪愆,于轻快的音乐旋律中执着地舞动。

—“要我说,生命充满虚无。” —“嗯,死亡是件大事。一个人死了,他要做的事情都完了。” —“我一直在思索死亡。我想说,一个人怎么死去呢?他呼吸减慢,然后直到他再也呼吸不了了,接着他就停止......他死的时候自己知不知道呢?” —“去去去,问别人去,你看我像是死过的人吗?” 思考是时髦的,闪躲总是结尾。此种游移的艺术被这一阶层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帕索里尼是愤怒的,在影片拍摄前不久的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后,他怒斥了大会冠冕堂皇的自由宣言,声称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是神话的自由,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自由,最终会变成平庸的托词。 意识形态在衰落,马克思主义不复存在。托托父子遇到了乌鸦,它的自我介绍趣味中夹杂着刺点:我来自一个叫意识形态的国家,我住在首都(与资本构成双关),一座未来城市,在卡尔马克思大街,七十乘七号。此处是帕氏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无奈的自嘲,但却不像伍迪艾伦一样含着自怜,而是体现为一种冰冷的科学式解刨,有着更客观也更深沉的力度。这位马克思主义最后的旗手为二人讲述了一则寓言:两位修士分别使得大鸟(鹰)与小鸟(麻雀)皈依基督教,但仍旧无法改变鹰吃麻雀的本能。传教者愈是虔诚而聪慧,结果愈是可笑而荒诞。末了,圣弗朗西斯以信仰上帝来搪塞二人。帕氏以此隐喻一种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关系,一种理性主义(更加马克思主义化的理想)和“野蛮”思想的对峙。弱肉强食,基督的博爱思想在这法则面前束手无策,徒留一丝悲凉。 帕索里尼在阐释一种真正的危机,它涉及马克思主义的陨落、无辜百姓的牺牲、知识分子的死亡、消费主义的肆虐、语言表达的退化,以及最重要的,对未来的人类之路的迷茫。托托父子最终吃掉了乌鸦(图1),这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临终献祭,另一方面也是知识分子与大众强制融合的象征。无论人们在何种程度上吸收、同化了他们,知识分子的消亡确是最真切的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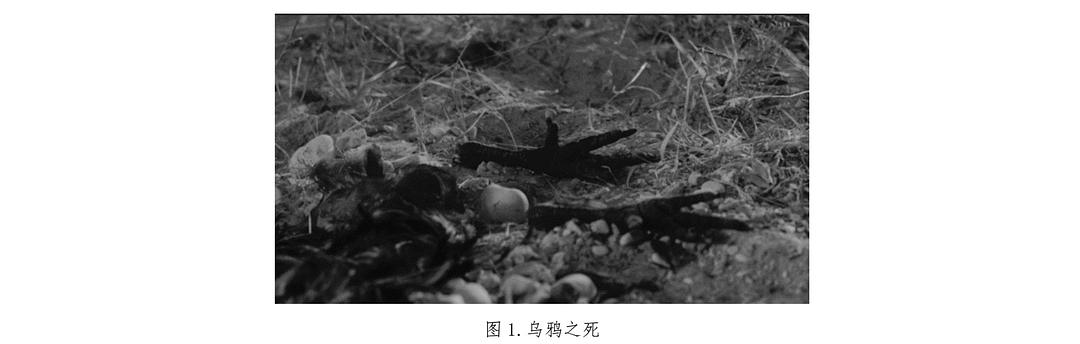
影片中乌鸦的闲语揭示了帕氏矛盾的情感。它艳羡父子能在城郊的小路上闲庭漫步,伴着阳光走进咖啡馆,用最平实的语言讨论生死,暗示帕氏对田园平淡生活的向往。但他又对这种妥协的生活态度报以不屑,以批判乃至苛责的眼光审视大众的行为方式,以知识分子的口吻进行揭露,就像乌鸦嘲笑托托把避孕膏当药膏涂抹脚疮一样,其结果必然是吃力不讨好地招来质疑与谩骂。人们毕竟更愿意生活在想象之内,满足于梦境之中。而帕氏从不愿意放过自己。 电影的体系由两个平行的轨迹相辅相成,除了对现实问题的悲观挣扎,还有对电影之路的思忖。 托托父子符合新现实主义人物经典的特征:意大利的芸芸众生之一,听任时光流逝而从不去思考。影片第一部分有两个极具辨识度的片段,一者是父子与群众一起观望模糊的社会性事件,一者是儿子奔赴带着翅膀道具的女友,它们分别召唤着罗西里尼和费里尼两位新现实主义巨匠。在前者,帕索里尼以一连串的目光镜头(单人—双人—群体),连带着荒凉的破败建筑构图提示着新现实主义(组图3),而与这一电影运动的辉煌紧紧相连的根基——社会批判以及对细小微光的发掘,却被帕氏故意隐去(整个片段对可能的惨案都遮遮掩掩)。此处的寓意是清晰的:当一类电影仅凭镜头风格即可辨识,也即意味着其真正的消亡。正如帕氏所言,意大利已然进入了经济繁荣,全民工业化的时代(片中飞机略过乡野的镜头便是最直接的体现),新现实主义电影走到了真正的穷途末路之上。而电影何去何从?后一片段(加之影片尾部的小丑奇遇)传达了费里尼的探索,他极力挣脱新现实主义的桎梏,从超现实中寻找新的切口,直达人的心理感知,即使天使女孩狡黠的笑透露出了帕氏的痕迹。但帕索里尼本人的道路更加独特艰险,他只想把摄影机锁定这现状本身,以强烈的自省力不断抛出本体性的质问。

托托的服饰使我们联想到卓别林的电影。大量使用的降格片段(默片的标志性手法)不但没有走入弄巧成拙的陷阱,而是为影片增添了一丝苦涩的幽默。显然,帕氏在寻求与影像历史的互动,保持着对默片传统的敬畏与质疑。在片尾,那位身材娇好的女郎露娜(图2)吸引了父子的注意力,这何尝不是对费里尼的又一次提示呢?这一搭讪片段显得活力十足,它紧接在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葬礼的记录影像之后,而在此之前,父子正被大资本主义家的猎狗压在蹄下。这是绝妙的讽刺,提醒我们保持对记忆问题的关注。人们的记忆一向不好,我们只是面对今天发生的事,也只有这瞬时的记忆。任凭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牺牲,群众的目光依然被欲望带到应去的宿命。他们不想被打扰。

“电影已死”至此在两个维度上被不断强调。在表层上,新的影像作者沉溺于编织意识形态的谎言,于二十一世纪继续扛起复兴向上的虚幻旗帜,以衰颓之态佯装伟岸之姿。另一层面,即使如帕索里尼这样的清醒者成功破除往日的神话,通过一种正确的误读误用,使得电影具备多元的思索导向和复杂的辨析精神,艺术家本人却深陷泥潭,无法给出现实的解决。大众抵制倾向、艺术家存在危机、影像自身的悖论互相缠绕交织,预示着未知的荒芜。 我们无能为力,帕氏在临终如是警告。 人类将何去何从?帕索里尼并不能提供答案,但他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真诚。影片成功的秘诀在于恰当地使用突兀,以一种敢于揭露高贵中的丑恶、同情中的鄙视之勇气,刺穿人类走向衰落时的矫饰。 什么是最成功的喜剧?至少你不能忽略一部把《喀秋莎》变成丧曲的影片。
原文地址:
乌鸦在行走,乌鸦会说话,乌鸦告诉他们13世纪的古老故事,乌鸦和他们一起经历20世纪的现实遭遇,但是最后乌鸦却说:“已经走到头了,我的人气数已尽,语言已经进入虚无,另一个人将会出现。”于是,身为父亲的托托悄悄对儿子说,肚子太饿了,把它吃了吧。而儿子尼诺并没有阻止,也没有逃离,于是两个人折回——在最后路旁剩下一堆乌鸦的骨头和羽毛之后,父子两个又继续前行。
路途还在前方,方向似乎还未明,托托和尼诺父子如果在吃乌鸦之前作出决定,他们也许会以不同的方式结束旅程,“路途刚起步,旅途已结束。”这是父亲对儿子说的话,在遇见了各种人物,各类事件之后,托托和尼诺父子俩走在那条路上,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像是没有了希望,对于他们来说,向穷人征收费用和被富人逼迫讨债成为双重目标,而这双重目标其实是连接在一起的,在那处穷人家里,他们看到了一个从屋顶上下来的妇人,走进屋子,是一个坐在凳子上面无表情纹丝不动的男人,又传来楼上孩子叫妈妈的声音:“妈妈,我好醒来了吗?”妇人告诉她:“天还没亮,再睡吧。”天其实已经大量,只是妇人不让孩子起来的唯一原因是,起来要吃饭,而家里没有了粮食。所以当父子俩要在这里征收费用,妇人似乎哭泣着说:“我们实在没有东西,我们已经身无分文了。”托托建议卖掉地皮,妇人又哀求他们,没有办法的父子只好走了出去,而房子里,楼上的女孩还一直叫着,妇人拿着尼诺所说的“燕窝”摆到桌子上,男人则把椅子移过来吃了起来。
燕窝当然不是燕窝,费用当然也没有征收到,而他们进入但丁牙医协会的聚会场所,找要他们还债的工程师,几条恶狗扑向了他们,被恶狗控制住的他们说自己没钱,没有粮食,而且托托说自己还有18个孩子,于是工程师最后警告他们:“25号是最后期限。”征收费用他们一无所获,被迫还债又身无分文,夹在两者中间的父子其实在更高的压迫者那里也变成了穷人,妇人一家的命运在他们身上重演,于是,饥饿的他们,走投无路的他们,看不到希望的他们,把唯一的乌鸦吃掉了,就像那碗“燕窝”一样,只是某个满足欲望的符号,而走在路上,他们无非是在做出了判断的“路途刚起步,旅途已结束”的状态中又回到了命运的起点。
找不到出路,是父子的唯一命运,这个夹在中间的阶层既不是可以完全用武力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也不是占有生产资料和资本的资产阶级,这种尴尬的处境让他们只能通过一只小小的乌鸦来满足欲望。但是乌鸦之毁灭,绝不仅仅是一个空泛如燕窝的符号的破灭,而是具有复杂的隐喻性。乌鸦是在父子俩走了一段路之后出现的,当乌鸦出现时,托托就说了那句话:“路途刚起步,旅途已结束。”这就是一种在毫无希望中看见希望的开始——最后乌鸦说:“语言已经进入虚无。”而在相遇的那一刻,乌鸦会说人话,可以理解是父子听懂了乌鸦的鸟语而重新产生了希望,也可以理解乌鸦听得懂人类的交谈而成为人类的一员。但是这种乌鸦到底是什么?托托问它是先知吗?是警察吗?乌鸦却建议他们去找人算命,乌鸦既不是关于信仰的先知,也不是关于社会秩序维护者的警察,对这两重身份的否定,以及让他们去找人算命,便是乌鸦新的、潜在的身份,这个身份是在乌鸦讲完了13世纪的那个故事之后,出现在字幕里的:“乌鸦是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时代的左翼知识分子。”
陶里亚蒂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继承了战友葛兰西“阵地战”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理论,而且把社会文化斗争的作用体现在集体的知识分子身上,从而夸大了它的地位,而且之后还提出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用改革内部结构的方法取代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从而通过和平走向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个关于陶里亚蒂时代的字幕的提醒,多少有些直白了,它直接将整部电影的主题显露出来,那就是帕索里尼对于左翼知识分子的一种批判。而自己曾经作为左翼知识分子,而且是葛兰西理论的支持者,帕索里尼为何在电影中开始了对这一思想的批判?如果去除字幕的提醒,这个有着政治寓意的故事,其实充满了哲学情趣,它在解构和建构、戏谑与戏弄中,充分运用电影语言,针对现实问题提出了非常有创建性的观点和启示。
乌鸦是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乌鸦自己也说,它是从“理想国”而来,它的父母是“疑问”和“觉悟”,“理想国”在哪里?乌鸦说,在卡尔·马克思街,于是父子俩大笑,“那是文盲的殉难处。”这是一种讽刺的开始,之后父子分开道路行走,但是彼此却能听到说话声,实际上这是为接下来乌鸦讲述十三世纪的那个故事做了铺垫,因为其中跟随圣弗朗西斯的两个圣徒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传道问题——乌鸦开始将他们带入到位于卡尔·马克思街的“理想国”之前的信仰世界,它说的便是:“你们的无知和仁慈都没有宗教意义。”在13世纪的故事里,老的信徒叫西西诺,他代表着仁慈,小的信徒叫尼内托,他代表着无知,他们的任务是对鸟类进行传教,而要对鸟类传教就是要让鸟类听得懂说话,就是让鸟类知道上帝。
无知的尼内托说:“我连和人都无法交流。”于是在整个过程中,他要么和小孩子嬉戏,要么被城堡里的男人扔来扔去游戏,要么在四季变化中装模作样祈祷跪拜,要么在集市里和女人、商人、魔术师玩耍,要么在空地上玩跳房子游戏。无知者无畏,他当然无法懂得宗教的意义,而仁慈的西西诺呢,他是虔诚的,他期待奇迹的出现,春天的花开了,他跪在那一座废弃的城堡面前,夏天的风吹来,他还是一动不动地跪拜着,秋天树叶凋零,他还是一如既往,冬天飘起了雪花,他也不怕冷,接着春天又来了,在春夏秋冬的一年之中,西西诺保持着同样的姿势,不说一句话,终于他开始和老鹰对话了,天上的老鹰围着他飞翔,他们开始对话,而对话对于西西诺来说,就是传道。
传道的唯一核心词便是:爱,老鹰问他:“你是谁,你要什么?”西西诺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创造物。”老鹰又问他:“谁是上帝?”西西诺说:“上帝。”于是最后西西诺告诉老鹰,上帝的意义就是让人们得到爱,于是从来不知道上帝的老鹰开始重复着那个词:爱。对老鹰的传道顺利结束,接下来他们又要对麻雀进行传道,西西诺希望不要像和老鹰说话那样难,但是当他跪拜在房子前面的时候,周围集市的嘈杂声、尼内托的嬉戏声又干扰了他,他终于愤怒了,将集市里的摊子打翻,还惩罚和鞭打了那些人,于是在人群做出举手投降之后,西西诺再次投入到和麻雀对话中。但是他始终无法听懂麻雀的叫声,这一次是无知的尼内托帮助了他,他正在玩跳房子的游戏,西西诺忽然醒悟:麻雀就是靠跳跃来说话的。于是他和尼内托一起跳跃,果真,在房子上的麻雀开始和他说话,麻雀说自己这几天没有粮食吃,而西西诺答应自己和尼内托斋戒,把粮食给他们,最后西西诺也告诉他们,这就是爱。
西西诺的虔诚和仁慈,尼内托的无知和跳跃的启发,终于使他们完成了向鸟类传道的目的,似乎也是功德圆满,但是乌鸦当初说他们的物质和仁慈都不是宗教,也就是意味着宗教在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看来是无用的,而且事实果真如此:一只老鹰从天空俯冲下来,把正在田里觅食的麻雀抓住了,然后开始饱餐一顿。见证了这一幕的西西诺大为吃惊,他向老鹰布道,传递了上帝的爱,他向麻雀布道,也传递了上帝的爱,但是为什么懂得了爱的老鹰还会残杀同样懂得了爱的麻雀?这是一个互相残杀的结果,这是无法解决的矛盾,在那一刻,西西诺仁慈发生了动摇,信仰受到了威胁,所以他只能求助了圣弗朗西斯:“他们相互残杀,我能做什么?”弗朗西斯告诉他的是:“上帝会帮你们任何事,这世界需要改变,这是你们未参透的,世界需要的是正义,需要的是消除不平等,不管是物种之间,还是国家之间。”
“重新上路吧。”这是圣弗朗西斯最后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当爱无法制止自相残杀,当信仰无法化解强者和弱者矛盾,只能用“继续上路”的方式探求解决之道。十三世纪的故事在乌鸦口中被讲出,实际上就是一种对宗教的否定,不是无知和仁慈都不是宗教,连爱本身也在不相等的物种之间变成残杀,而回到现实,是不是乌鸦的理想国会带他们解决压在他们身上的双重困难?是不是疑问和觉悟作为父母会让他们走向光明之道?这里不妨从乌鸦口中的十三世纪故事脱离出来,回到父子出发的那个起点。在遇到理想国的乌鸦之前,父子俩其实就是走在一种现实里,就是遇见了没有答案的社会问题:他们看到了不同的路牌,“通向爱哭鬼托尼托之家,待业。”“通向贪吃鬼安东尼奥住处,保洁员。”“撕被单的利路之家,12岁逃离家乡。”……这些路牌注明了那些现实中的人的生活状态,他们都在底层挣扎着;父子经过被很多人围着的地方,大家沉默着,面无表情,父子最后看见有人被抬了出来,这是有人死了,于是尼诺说:“生命充满了虚无。”而当他问托托,死亡是什么时,托托也说出了死亡的阶层性:“富人在坟地里安息,还会放上金币,而穷人微不足道。”之后尼诺去找人玩,他看见了穿着天使衣服的女孩,女孩说,她要在修道学校表演戏剧,于是在楼上的窗口、门前和走廊上,女孩像一个天使一样出现,现实里没有天使,天使只不过是一种戏剧表演,于是宗教在现实里被戏剧化,甚至戏谑化;两个人继续走着,走到了一处立交桥上,桥上没有汽车,也没有行人,在城市进行大规模建设的时代,空空的立交桥象征着资产阶级追求物质主义的生活。
在没有遇到乌鸦之前,父子俩看见了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只是一种静态的展示,当理想国的乌鸦到来,社会矛盾又将如何被化解?乌鸦讲述了十三世纪的故事,并不是为了否定宗教的意义,而是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解决方法,那就是消除物种和物种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但是何处是正义?身为理想国的乌鸦,代表左翼知识分子的乌鸦,帕索里尼显然是持批判态度的,而且乌鸦在讲完故事之后,父子俩其实不是正义的到来,而是社会问题变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动态问题。他们因为内急寻找厕所,终于在田野的草垛旁开始解决,不想被附近的农人发现,说他们侵犯了私人财产,于是他们拿起了猎枪,朝他们射击,本来父子在被阻止之后曾用皮带抽打他们,于是矛盾被激化,“为了一小块地,战争爆发了。”战争如何发生的?是源于私有财产被侵占,是源于暴力取代了宽容;之后父子就走进了穷人家里,托托要让他们把地皮卖了,这分明就是一种欲望使然,而这种欲望加深了阶级对立;之后他们遇到了几个路人,一个老人请他们帮忙推一辆卡迪拉克,这里其实折射出美国资本主义的虚伪,老人为什么叫他们推车,是因为他说这里的人都有病,除去腿有伤的那个男人,其他几个基本上不算有病:一个人患了痔疮,一个女人是孕妇,而另一个则是因为刚做了指甲护理,于是父子帮他们推车,而在这时,女人忽然肚子痛了,于是便在车后面生产,一会儿一个白胖胖的孩子降生,于是大家放烟花庆祝,并将孩子命名为“欢迎”。
凯迪拉克、讲英语的女人、以及黑人白人在一起的群体,似乎隐喻着美国社会,当黑人白人一起推车,当主人客人一起努力,是不是就是美国的民主?民主能解决社会问题吗?似乎也是一种虚伪,那些人的病其实不算是病,而那个女人拿出一块牌子上写着:“罗马是如何毁灭世界的?”当托托抱怨自己脚上长了老茧之后,他们说自己有特效药,于是一千块钱卖给他,而当他们生完孩子开着车走了之后,乌鸦告诉他们这根本不是治疗老茧的特效药,而是避孕药,托托好奇地问:“什么是避孕药?”乌鸦便问他:“你有几个孩子?”托托回答:18个。18个孩子,不知道什么是避孕药,还被骗走了一千块钱,这一幕荒诞剧似乎就指向了意大利贫困问题:是因为愚昧无知不控制原始欲望,是人口增长导致资源枯竭,所以贫穷,所以没钱,所以本来是征收费用却成为身无分文的欠债者。
争夺私有财产到暴力争斗引发战争,被丧失人性导致阶级压迫,团结一致却是一场虚伪民主,而最后两个人走在路上,遇到的是在路边名叫露娜的妓女,父子终于在禁不止诱惑,先是托托以肚子痛为由钻进了玉米地去找露娜,露娜让他闻“菠菜和肉汤的味道”,后来是尼诺也是同样的理由钻进了玉米地,找到了露娜说:“你的乳房真美。”一种欲望荒诞剧在父子之间上演,远处降落的飞机似乎也暗示着最后两人都得到了满足。而这一切都是乌鸦存在时发生的场景,但是乌鸦只是乌鸦,它只是见证者,只是同行者,只是旁观者,一只理想国的乌鸦,一只气数已尽的乌鸦,一只也根本无法消除不平等的乌鸦,最后的命运似乎只能是被吃掉。
宗教信仰中的爱,无法避免互相残杀的悲剧,来自理想国的乌鸦无法提供消除不平等的办法,所以意识形态王国的卡尔·马克思主义,在帕索里尼那里只能在“语言进入虚无”中变成充饥物,而父子俩到底会走向何处?帕索里尼引用毛泽东和斯诺交谈时问的一个问题:“人类将何去何从,谁知道呢?”宗教失去意义,马克思主义无能为力,人类到底走向何处,帕索里尼只能用一种虚无主义设置了永远的问号,也许,乌鸦所说将会出现的“另一个”是另一只乌鸦,来自理想国,描绘乌托邦,最后在人类的贪婪中变成一堆骨头和羽毛。
影片以极其幽默的方式朗读演职员表开头,全片呈现出一种轻快有趣却处处发人深省的风格。特别朗读的演职员“哲学顾问”也说明本片承载了帕索里尼很多的哲学思考。影片中间,为防止观众没有跟上,帕索里尼还特意用与观众互动式的对白点明了乌鸦的所指,一个意大利共产主义浪潮时期的左翼知识分子。
“-人类将去往何处?-谁知道呢。”开头的一句斯诺与毛主席的对话引用已然将这个类公路片放在了人类命运的大课题下,接下来影片中的每一个情节已不再是它本身,而更多的是一种隐喻或象征。
第一部分的老鹰与麻雀,讲述的正是左翼知识分子构建幻想中的乌托邦的历程,他们做了极大的努力,让上层与下层阶级都接纳了爱的思想(导演在这里设计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即不同阶级的沟通语言不同,不同阶级之间在交流上存在天然屏障),却难以解决现实中阶级本身的存在。他们的梦想是伟大的,但在没有方法的情形下(圣人模糊所指的教导),也是天真的,是易碎的。现实中的阶级差异无法消除,战争也就连绵不断,全人类爱的皈依永远是童话故事。
第二部分则是在第一部分的寓言讲述后,转入现实世界的写照。父子俩为解决内急,在侵入了他人的私有财产后,因双方的暴力而引发争执和打斗,正反映了世上的战争爆发的原因。父子俩后又在下层阶级处讨债,即便妇女已多次申诉自己的痛苦,父子俩仍不依不饶,态度凶狠(有趣的细节是那坐视不管只等吃燕窝的丈夫)。而一转眼,父子俩原也是欠了上层阶级的钱,有钱人对待他们时的言语正和他们对待下层人民的言语如出一辙。阶级压迫永无止境,被压迫者转而将枪指向更弱者。帕索里尼在影片接近结尾处插入了一段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公开葬礼的纪录影像,紧接着父子俩就把代表着左翼知识分子的乌鸦吃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就此落幕,它包含了一个圣洁而飘渺的梦想,一群传教士般坚毅的左翼知识分子,一些坚如磐石无法击碎的阶级壁垒,无数压迫与被压迫者的无尽轮回。最终,知识分子为人类殉道,而人类又将去往何处?
在镜头语言上,帕索里尼频繁使用大特写与全景的相互切换。整部影片因要承载的太多,而略失去其叙述的连续性。但其特别的风格,以及帕索里尼想借此阐述的自省与思考,都使影片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魅力。正如帕索里尼所说,文字是有限的,而电影能够用现实来反映现实。





